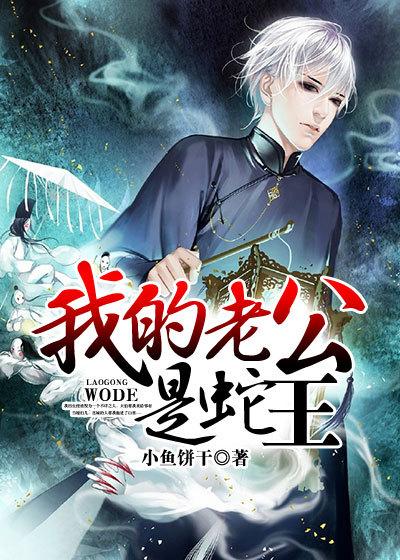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掌柜假娇媚百度资源 > 第75页(第1页)
第75页(第1页)
“中秋那日,儿子前往西淮坞布施,姜柠说她回姜府路上途径此处,恰巧瞧见我。”刘清洵将手中盏盖扣上,轻笑了声,“可问题是,西淮坞坐南,姜府朝北,两地相隔数条街,如何也不会是途径路过。”
“所以?”德妃心下揣摩了几分,未明其意。
“所以,她出现在西淮坞绝非偶然,亦并非一二次便可轻车熟路。不正说明她和儿子一样,经常去那地界儿行善布施么?另外,”他停顿了下,眸眼清隽,漫了丝浮华的光,“遇刺那晚,她还救了儿子一命。”
德妃显然吃了一惊,未等回过神儿来,又听刘清洵分析道:“她既心地向善,且胆大心细,懂眼力,知进退,无论将来儿子是何身份,这正室的人选,她都是最合适的。”
————————————————
城郊外,晏芝林。
日入晦昏,穹宇斜捎了层浅薄的黄,裹挟着金针似的亮丝,刺透软绵成团的缎云,蛰伏在叠嶂横卧的山峦上。
不过盏香更迭的功夫,日更沉,坠了丝绒的天幕里,渐浮渐逝。云梢褪黄,染漏霞涌,淌了橙红出来,如醉意朦胧,滚烫酡容。纷掩的松涛亦涂惹了那抹红,混沌如磷火,细瞧方觉,原是摇挂岌岌的落叶红枫。
晏芝林深,有马蹄哒哒仿若溪边暮砧,轮声辘轳,曲折蜿蜒了无尽车痕出来,道道深壑皆示载物之重沉。
这是一趟走苏北至京内的镖车。
前后各骑有数十镖师相护,中驭一乘四马套车。车身通漶墨黑漆色,外披同色暗纹麻布,束以一指粗的麻绳捆拢,尽是内敛低调之意。
棚顶支三角红纹勾边小黄旗,上书“邬”氏隽逸字样,内行的一眼便知,此趟镖物乃西山镖局所保。
镖队徐徐缓进着,行在队伍最头里的便是此行走镖的镖头,未见寻常那般彪型野汉,唯有一清影单薄的紫衣女子,持剑跨驹,身骨伶伶。
瞧那女子目光沉着玄霜,别样寡冷,眼风凌厉似隐泛青光的刀尖儿,沾霜肃肃。
自入林中,她便瞬时警惕异常,紧握着剑柄的指骨泛白,提着十足的戒备。
这倒也不奇怪。
常年跑商的镖头皆知,此晏芝林地势错综复杂,素来是个三教九流,泥沙俱下的混杂地界儿。饶是西山镖局这般响的名号,也几次三番地历了惊险,折兵损将亦是不可免却的事。
倏尔,蛙鸣止默,雀鸟振翅惊跃,寂叶逶迤而晃,簌簌沙沙,飘零起落而扬飞尘。
紫衣女子敏锐觉察到异样,旋即勒了缰绳,左手握拳抬起,示意停止前进。而后耳骨微动,黛眉紧蹙,低垂了眼帘,细细感知这死寂里细若游丝的窸窣声。
末了,骤然一道狠戾的刀锋自其身后挥劈而来,紫衣女子螓首微侧,冷幽的眸子稍眯了眯,如浸透浮冰般挂着阴寒。
但瞧她撑掌借力一跃,足尖轻点马背,登时身子倒挂腾空而起,从容避开袭来的刀刃。继而一个飞旋,双腿似青藤般紧紧勾缠住贼人颈项,只勾唇冷嗤了声,执着剑端迅速朝其小腹猛捣下去。
那贼人受创欲吐血之际,却被肩上女子扯了纶巾绷捂住嘴,下一刻,只见她两指轻捻纶巾往下用力一扥,直接将人活活勒死后,一脚蹬踹出去。
就在紫衣女子轻盈落地之时,已有大片劫匪包抄上来,将其镖队整个围住,死堵了个严实。
————————————————
醉春楼。
初秋露重,正是蟹肉肥美酥嫩的时候。
醉春楼隶属宝昌商行底下,每年这会子酒楼里都会进一批闸蟹来,因着是京中最早到又鲜得很,陆绍人会趁势将价格抬高两成,且每人限次限量不可批购,惹得各富庶世家提前半月便涌来排了队预定。
不得不说,那奸商虽看着吊儿郎当没个正行的样儿,到底还是个能谋善断的。姜柠也是这些年在他跟前熏陶着,对商道上的事稍微开了点儿窍。
牙尖儿磕了两下蟹钳,纤指娴熟地剥了碎壳下来,露出里头嫩白酥软的肉条儿,姜柠正要往嘴里递,却不料蓦然凑了个头过来,直接一口叼走了她手里的蟹肉。
“嗯,嫩得很~”陆绍人桀佞不拘地一屁股坐了对面,嘴里边儿嚼着满意道。
若不是此刻旁桌儿都满着客,姜柠定要将手里剩下的空壳扔他脸上,无奈要在外面端着矜持,只好暗狠狠地白他一眼,故意奚落道:
“这蟹虽嫩却也金贵得很,您这一口怕是要吃掉我三两银子,陆掌柜可真是抢钱的一把好手。”
陆绍人邪痞痞地扬了扬眉,笑得浪荡,“就是金贵才显得嫩。”说着,朝她招了招手。
姜柠瞅他那副玩世不恭的样儿就来气,但嫌弃的同时,还是稍往前抻了抻脑袋。因为她知道往往这时候,这奸商总会扔出些经商语论出来,而这些正是她想学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