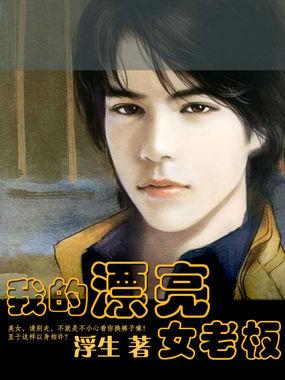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山鬼花钱是什么意思 > 第51页(第1页)
第51页(第1页)
在那般绝境中还能被海浪卷到岸边,大概是老天仍怀仁慈之意吧?沈桐儿憋住迷茫的眼泪,明白只有魂尘才能帮苏晟寻回生命力,不由俯身摸住鸟儿说:“我……去看看附近有没有异鬼可以抓……”苏晟冥冥中有所感知,声音虚弱地阻止:“不可以……”“你熬不过去的!”沈桐儿已经不在乎自己的皮肉伤了,她坚定地说:“别小看我,之前自己也杀过很多异鬼,我肯定能治好你!”苏晟喃喃道:“不要走……”沈桐儿心生片刻犹豫,考虑到如果遭遇太多饥饿的异鬼,自己有可能没命回来,那样彼此便见不到最后一面了。外面的雨似乎比方才温和了些,却仍不时回荡起雷音。最后小姑娘一咬牙,决定说:“好,那我带你一起,就算死咱俩也在一起好不好?“这回苏晟终于没了反应。沈桐儿深喘过气后,便再度将它背在身上,顶着暴雨夺门而出。——从前与异鬼战斗是为了自保,而今却要把它们当成食物。心中有了杀意后,整个人的手段都变得不同了。但沈桐儿并不犹豫、也不后悔,因为至少此刻,让苏晟活下去对她而言比什么都重要。这个不懂太多道理的姑娘终于明白了云娘所言“众生无别”的道理。原来在私欲面前,自己并不比异鬼更高尚。傍晚忽至,暴雨终于停歇。运气还算不错的沈桐儿在林间连捉住两只落单的异鬼,也不敢更多恋战,又带着战利品回去了废镇。她将其魂尘给鸟儿服下后,就在那间破屋的外面打来清水、支起篝火清洗起破旧的衣服。由于逃命太过匆忙,许多行李都弄丢了,随身携带的东西里完全不存在食物和药品。沈桐儿虽然饥肠辘辘、却又精疲力竭,坐在房檐下感觉自己再也折腾不动,终于抱着白鸟闭上了沉重的眼皮。她因烧伤而隐隐发着低烧,浑噩的梦里一会儿出现安宁的芳菲岛,一会儿出现无边黑暗的海底。浸在此起彼伏的思绪中,竟便如此跌入夜色深渊的尽头。——亘古不变的海浪不停地翻涌,将浮在水面上的木板冲击得上下晃动。早就于海难中失去意识的齐彦之缓缓睁开眼睛,凝望过漆黑的海水后,猛地仓皇回神、发觉妻子仍在身边。“容儿、你怎么样了?”他急着跳入水中,让开位置把吴容完全推至木板,扶着她那鼓起来的肚子冷汗直冒。身为御鬼师的吴容比普通人都要坚韧些,此刻竟还留有余气,小声呻吟:“彦之……我好冷啊……”齐彦之四下瞥见遥远的海岸,忙道:“我带你上岸,等着、等着!”就在这个时候,他们附近的忽而响起低沉的声音:“人类都是这般言而无信吗——”齐彦之脸色大变,瞬间回头对上鲛王蓦然出现的恐怖巨脸,结巴道:“饶、饶命!”“我把灯借给你们,是为了保她平安,你说过隔日便会还回来。”鲛王冷冰冰地质问:“结果之后,你再未来过长海。”齐彦之当然心虚:“因为容儿她身体不好,所以我才迟了几个月……”“若不是被挟持,今日你当真还会来吗?”鲛王全是都是青色鳞片,在月色下闪着奇异的光,它比两三个壮汉还要高大,甩着巨尾瞬间冲到齐彦之面前:“听说你在岸上卖鲛膏?哪里来得鲛人,又是什么东西做得油膏?”齐彦之搂着吴容渐渐泛冷的身躯,快要被它吓得昏迷过去,终于承认道:“我绝对不会伤害您的同类!只不过把些流难的女子砍断腿后,和南水河北边的银莲鱼的尾巴缝制在一起,去欺骗那些蠢人、讨点生活的本钱而已。”鲛王的眼珠没有眼白,纯粹的黑在月色下格外惊悚。它摇头叹息道:“残害同类还说得这般理直气壮,我真后悔救过你!”“可是同类于我无恩、只有恨!在这纷乱的世道里,比异鬼更可怕的就是人心啊!”齐彦之苦苦哀求道:“我明白自己死不足惜,但请您救救我的妻子和孩子吧!”鲛王冷笑:“你以为我是什么?鲛人?神明?还是恶魔?”齐彦之沉默片刻,回答道:“您是这长海的主人!”“我也是异鬼!你究竟在想什么!”鲛王忽然用大手掐住他的腰,把他举离了微凉的海水:“是长海养育了我,长海才是我的主人!”齐彦之被吓得抖成筛子,哆嗦着讲不出半句话。鲛王伸手把他丢到水里::你毁了母亲的灯!我不会再为了救你而惹怒她,是死是活都是你的命,再与我无关!”话毕它便迎着月光一跃,在被激起巨大的水花中消失无踪。齐彦之狼狈地苦苦挣扎之后,终于再度扶住了吴容所在的船板,他拼命地用手滑动,只觉得四周已被异鬼低沉的嘶吼所包围,却又没阴阳眼可以确定,不禁抬头对着天空发出了绝望的惊叫!——曾经看起来那般强大而荣华的水商行竟然在一夜之间毁于一旦,这件事情简直比它的出现还要离奇。被季祁威胁住的吉瑞没得选择,见此人也并不是长湖匪患一伙,便忍住眼泪,将妹妹悲惨的遭遇倾吐而出,然后哽咽着说:“所以无论如何,只要能找到齐彦之,我一定亲手会宰了他!”季祁听得面色凝重,扶住胸口的伤痛处悲叹:“没想到一桩惨事未了,人间又添新灾,不知还有没有尚且存活的女子,复仇事小,现在更该做得是给她们寻条生路。”吉瑞身子微微一震,不禁羞惭于自己的心胸狭窄,点头而后疑惑:“你到底是什么人?”“我的身份自己也没资格告诉你,你只需记着,我在为百姓好便是。”季祁咳嗽着拿起桌上长剑,准备出行。吉瑞慌忙阻拦:“且慢,外面乱作一团,大哥你负伤如此之重,还是……”季祁叹息:“没有选择,死而后已。”说着他便推开门,示意忠诚守在外面的御鬼师跟上自己。无处可去的吉瑞赶忙尾随在后面,与他们一同出发寻找受难的女子。——事实上水牢里的“鲛人”全被花病酒放了出去,她们本就失血过多,加之没有隔绝河水的铁箱保护,已然全部被淹死在河底,不能不说是无意间办了件大坏事。已迟太多的季祁自然扑了个空,兜兜转转之后,竟带着亲信与吉瑞到达停工的油坊。为确认心中残酷的猜测,吉瑞忍着反胃将一只尚未焦熟的“鲛人”拖到地上,颤抖着双手检查早已腐烂的腰部,终于在肉里发现了精巧的缝线,她的心中被巨大的悲伤所击中,根本不无法想象那般善良的妹妹在死前究竟遭受了多么残酷血腥的事,顿时泪眼朦胧。季祁叹息:“别哭了,我们还是让这些女子入土为安的好,混账齐彦之被鹿家带走,多半要为此丧命了。”“为何人命如草芥,为何我们这么努力地活着,却还是卑微得连尘土都不如……”吉瑞捂住脸痛哭:“明明那么多残忍的家伙还活着,我妹妹却死了!”季祁过惯了粗糙的生活,不怕流血吃苦,却并不晓得如何安慰一个伤心的姑娘。正在手足无措的时候,外面隐隐传来悠长的口哨。立在油坊门口的御鬼师立刻道:“季大人,是鹿家人出现了,我必须要带您走!”“罢了,没想到这次暴露的如此之快,鹿笙果然诡计多端。”季祁皱眉:“花病酒没下狠手杀死我,姓鹿的肯定无法容忍,姑娘,你也随我们走吧。”“不,我要去找齐彦之。”吉瑞抹着眼泪拒绝:“我本与你们没有瓜葛,鹿家也不屑于多理我,没有跟你走的道理。”季祁皱眉:“可是附近不仅有鹿家,还有异鬼。”“异鬼是不会靠近我的,我不能放过欺凌雪儿的凶手!”吉瑞拱手道:“大哥既然不愿意真身相告,那便就此别过吧!”——微薄的晨光点亮了沈桐儿暂已藏身的废墟,她被照到眼皮,顿时从噩梦中惊醒,第一件能想到的事就是关心怀里的鸟儿。幸好服过魂尘又经过短暂的休息,白鸟的伤势已有好转,原本烧焦的皮肉开始泛红,开始长出了新的绒毛。沈桐儿万分激动,轻轻地亲了亲它的头,啜泣着说:“太好了,我还以为你坚持不下去了……那个长明灯怎么会如此厉害……”苏晟并没有回答,只是睁开仍旧纯洁的黑眼睛,默默地瞧着她。“看来我实在是太高估自己了,那赤离草注定不属于我。”沈桐儿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相信鹿家人,等你的伤势稍微好转,咱俩就回家吧。”苏晟依然虚弱地保持沉默。事情偏离了他原本预计的轨道,看来这十多年里,那些异鬼已经掌握住了更多关于它们自己的信息,接下来该如何是好,在此刻实在无法断然决定。沈桐儿依旧心思简单,站起身说:“也不晓得这是什么地方,看起来比那个破破烂烂的长湖镇大上许多,而且异鬼的痕迹非常稀少,走,陪我去前面找点水喝。”因为动作的拉扯,白鸟全身溃烂的皮肤开始剧痛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