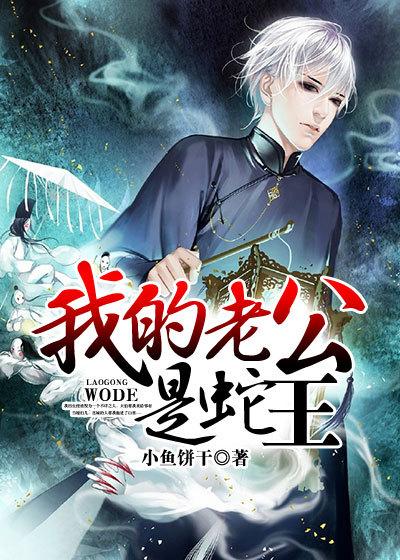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司法大楼图片 > 第九十八章 吉祥赌坊(第2页)
第九十八章 吉祥赌坊(第2页)
普通的赌场,一进去之后,都是烟雾缭绕酒气熏天汗味儿扑鼻,可是这里不然,虽然不清净,也不很乱,赌钱的客人虽多,但并没有谁高声喧哗,锦衣华服衣香鬓影之中,显出不寻常的秩序。
这是个有钱人的赌场。陈凡心想。他发现这里不独独有戴黑色网巾的赌客,还有带白色网巾的赌客,不单有嗜赌成性的中老年妇女,也有带面纱围帽的年轻女子。在明朝那个礼教严谨的年代,沮丧期间与年轻女子赌博,这可都是天理难容的重罪。若是被县里的书吏或者教谕发现,可是要问罪的。
“有些话就是专蒙刚出道的死脑筋,正儿八经的官家哪里会管这样的闲事儿,他们关心的只是咱家能交多少银子,一半给朝廷,一半进自己的腰包,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就万事大吉了。”眉娘冷笑着说道。
陈凡知道她在给自己这个生瓜蛋子下马威,赶忙赔笑:“在下自然比不上眉大当家的如此明察秋毫,受教了。”
眉娘一笑,领着他们往里面走,近距离全方位的观察这个赌场,赌场的大厅很大,里面赌的花样很多,有牌九、猜单双、打麻将等等,但赌的最多也最大的还是掷骰子。这玩意来钱快,也不用技术,完全凭运气,是外门汉的最爱。
庄家的手里已经连续开了十三把大,很多人都觉得邪性,寻思着应该开一把小了,于是几乎全都跟庄家对着压小,结果第十四把仍然开大。于是陈凡看到庄家用一把小耙子,把小山一般的银子收入了囊中。
此时外面忽然走进来一位穿着藏青色直裰的中年人,和他同来的还有两个人,手里提着很大的柳条箱。
大约是因为此人气度不凡,。这人宽肩窄腰,五官向外鼓出,个子高大骨骼生硬,眼睛虽小却散发着妖异的光芒,黑丝网巾上面是碧绿色的束发冠,双手带满了金戒指、玉戒指、翡翠戒指。腰带上的玉佩被风一吹,叮当乱响,发出清脆悦耳的鸣叫。
因为发黄所以才显得妖异,所有人都看出他是个西域人。
眉娘和龙威远全都是浑身一震,尤其是眉娘,立即撇下了他们两人,迎上前去:“贵客呀,真是贵客呀,我说这大清早的喜鹊就一直喳喳叫呢,原来是有您这样的贵客到来呀,贵客,请雅间奉茶吧。不知道您的汉语说的如何?”
那人一副满不在乎的倨傲表情,嘴巴咧到腮帮子上去,但汉语说的实在不好,南腔北调的:“你这里还算可以,啊,我有点满意,不像有些地方的人一上来就胡说九道的,有时候还胡说十道,爷爷打算在你们这里玩两把,爷爷是西域来做玉石生意的,箱子里有的是钱财,你们要好好地伺候。”
“那是那是,像您这样的贵客咱们从来不敢慢待,将来我们的钱程还要多多仰仗您呢。雅间里面景色正好,我把自己个出嫁时候的女儿红拿一壶过来,再找个窈窕的小娘子陪着,保准您玩的舒舒服服,乐乐呵呵。”眉娘轻浮的假笑。
大约是听到有窈窕的小娘子伺候,客商的眼中顿时精光爆射,满意地说:“最好是你亲自来陪我,我就高兴了。”
眉娘把他引入雅间,噗嗤笑道:“奴家年老色衰,配不上您这腰金佩玉的大贵人,我家女儿年方十六,红丸未破,又妖娆又会哄人开心,我这就把她找来——还有就是,您要什么人陪着玩,多大的盘口?”
“最少一千两,上不封顶。”身后提着皮箱的下人骄傲的说道:“什么样的客人无所谓,关键是输了钱不能着急,赌品要好。”
“好好好,我这就去安排。”眉娘笑吟吟的跑出来了。
陈凡见她一出门口,就靠在墙壁上深呼吸了好半天,这才冲着龙威远抛了个媚眼,往楼上去了。
“有好戏看了。”龙威远说道:“别人看着她迎来送往把客人哄的滴溜溜转,满嘴的没规矩,就以为她不守妇道。其实她天天做鞋,日日省钱,嗷的比谁都辛苦,是个很苦命的女子,我估计她自从男人死了到现在,有七八年没接触男人了。”
“这么专一,今年多大?”陈凡惊讶。
“二十二了。”
“那嫁人挺早的。”陈凡一算,十六岁出的门子。
“可就是有一样,这妖精出了名的爱捡便宜事儿,爱财如命,也不知道她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这世上的事儿往往就是这么奇怪,跑题了——”龙威远一笑:“你看着吧,那个傻乎乎的西域客商要倒霉了,等会儿出去的时候,会被她吃干抹净。”
随着一阵忙碌,雅间里面多了两位赌客,四壶酒,外带一副筛子。眉娘请陈凡和龙威远也进去看看。西域客商以为龙威远的气度就是他的敌手,于是催促他赶快下场,龙威远笑着摇头。
这时候,从外面的人堆里站起来一个人,年纪六十左右,眼睛和猫眼似的贼亮,穿着蓝色的粗布长衫,腰板挺的笔直,走路的时候,闭着眼睛像是在打盹,慢悠悠的走过来,随随便便就在西域客商对面坐下了。
“阿拉和侬赌两把,如何?”说的是上海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