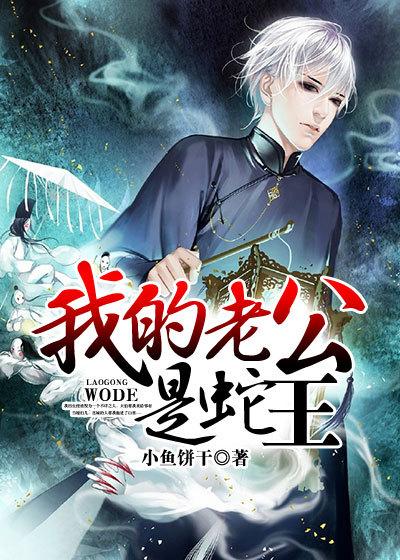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司法大楼图片 > 第四十八章 今见中山狼(第1页)
第四十八章 今见中山狼(第1页)
梅雪嫣穿着沉香色的袄裙,带着长沙围帽,长长的面纱垂到腰间,把上半身遮挡的一丝不露,围帽顶上露出用如意金钗绞的紧紧的发髻。其余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吴有才黑脸沉的像锅底,瞪着马郎中呵斥道:“夫人也让你见了,名节也坏的差不多了,你若是再治不好她,你小心点,我一顿板子拍死你。”
看着面纱缝隙中长长的睫毛忽闪两下,马郎中差点没晕过去,“大人,这可不是您升堂问案,摆摆官威,和了稀泥,就算完了。自古以来,医家救死扶伤,自有医家的讲究,蒙着面纱让我怎么看,等于没看?”
绿意怒道:“怎么,你还嫌看的不够清楚,我家老爷本着一片仁心,连官家的体面都不要了,你还要得寸进尺?我看你根本就不是正经大夫,就是个垂涎我家夫人美貌的老登徒子,老爷,把他乱棍打出也就是了。”
吴有才的脸拉的像吊死鬼:“官家夫人是你这种人能看的吗?看了我夫人又治不好病,按照大明律我打你一顿是轻的,挖了你眼珠子朝廷都不会怪罪,来人,把他给我乱棍打出去了——陈凡何在!”
得,陈凡一想,这地方除了他也没别人能轮的动棍子。
“老爷。”既然大老爷招呼了,大约就是可以进去了,不过为了一双眼珠子着想,他还是盯着地面膝行向前。
“快点,给本官照头照脸的乱棍打出去。”吴有才指着全身哆嗦大汗淋漓的马郎中说。
“小的做不到啊!”
绿意几乎是狞笑:“好啊你陈凡,亏了老爷如此的抬举你,你倒是会阳奉阴违,让你打个人你都做不到,难不成就只会打女人,老爷,这厮老大惫懒,分明和这个狗屁不通的郎中是一丘之貉,把他也打出去吧。”
“冤枉!”陈凡摊开空空如也的双手:“老爷说用棍子打,所以我做不到,还请老爷明鉴。绿意丫头分明就是挑拨离间,我看她根本不打算让夫人好,所以才在这里胡搅蛮缠为难大夫,老爷您是青天大老爷,可不能被小人摆布啊。”
他说这番话完全是因为不知道前面的戏码,不然也不会说这样的话。可是吴有才不这么想,他想,以前梅雪嫣仗着娘家的势力没少欺凌我,我厌烦了她想她死,可也不能做的太明了,太明了会落人口实,我的官声岂非要一败涂地,陈凡这话倒是提醒了我。表面文章我还是要做一下的。
“那你用手打!”绿意气道。
“小的还是做不到啊!”陈凡苦笑道:“老爷说让小的照头照脸的打,小的连头都抬不起来,如何照头照脸,能打到他的脚面就不错了,要不就凑合着打两下,也算是小的用尽全力为老爷尽忠了。”
吴有才暗想,这厮分明就是不想打。
“你的意思是老爷我这样的处置不妥当吗?”
陈凡暗想,梅雪嫣命悬一线,我总不能见死不救,那可不是本少爷的做事风格。吴有才这人还算是“讲道理明是非”,所以有些话我还要及时的跟他讲清楚。总要让他的封建脑袋开开窍的。
“老爷,俗话说事急从权,男女大防是要讲,可也不能让郎中做无米之炊呀。小的闭上眼睛打个人都费劲,更何况是让人家看病了,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再者说,《礼记》有云,男子四十可以从权,我看这位马郎中怕是都快七十了吧。此乃四十倍之,完全符合‘从权’的标准——”陈凡很想说‘就让他看看吧’,但仔细一想,这不是他一个捕快应该说的话,于是憋了回去。
绿意暗想,我也不是不知道‘事急从权’的道理,但今日是我咸鱼翻身的好日子,我必定要从中作梗,让梅雪嫣不死脱层皮,以后省的碍手碍脚,阻了我的青云之路,我拖的一时是一时,让她的病重的一分是一分,这才是上策。
她是梅雪嫣的陪嫁丫鬟,梅雪嫣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才女,耳濡目染之下,她也是半个知识女性。尤其《礼教》典籍,都是梅雪嫣平日里挂在嘴边的,她想充耳不闻也不行,近几年也可以说上那么几句。
于是绿意脱口而出说:“这可不行,《女四书》有言,男女三岁不同席,不共井,不共器,官家女子八岁不出中门,内言不出,外言不入,是为闺中典范,大家闺秀,至亲骨肉非有大故不入其门,
男子夜行以烛,妇人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男仆非有缮修,及有大故,不入中门,入中门,妇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仆无故,不出中门,有故出中门,亦必拥蔽其面。
就连我等这般女仆都不宜见生人面,更何况是夫人守身如玉的贵夫人,此事的确是万万不可。奴婢为夫人和老爷着想才如此说,我是跟在夫人身边长大的,知道她的心意,她把名节可是看的比生命重多了呀。”
陈凡撇了撇嘴心想,这时候的人脑袋都让驴给踢了,男人三妻四妾就是天道,女人被人看一眼就叫坏了名节。我去,谁能想到三四百年之后,“男女大防”就发展成了“见面上床”,那时候男人们也没脾气了,欣然接受了。以前倒也没觉得有什么,现在被这种思潮一冲击,我倒是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了,要走火入魔了。妈妈-的。
他深信吴有才是个好人,但也不能给他讲五四运动和女子解放吧。幸好他也是个饱学之士,知道“以毒攻毒”的道理,于是咳嗽道:“小的以前也读过书,唐代《白居易集卷六》有记载,白居易当官的时候曾经判过一案:一农夫在田间耕种,妻子送饭的路上遇到饥饿的父亲,就把饭菜给父亲吃了,丈夫等得饥饿,非常恼火,执意休妻,妻子不伏,告到官府。白居易判决说:按照坤德妻应顺夫,报答父恩根于天性;应该把饭先给父亲吃而丈夫在其后,尽管夫盼妻子送饭,但孝亲重于事夫,终于不予判离。
小的这话没有别的意思,小的听说夫人高堂尚在,活着应只为了尽孝道,本朝历代皇帝也都是最讲究孝道的,若是她因为固守着男女大防,先父母高堂而去,只怕孝道有亏,于‘妇德’方面是个大大的污点,按照白居易的理论来看,孝道还是大于男女大防的,夫人是知书达理的才女,自然明白这一点,想来是不会怪罪大老爷的了。”
吴有才的心里也在矛盾,一方面恨梅雪嫣在他面前假道学讲礼教,所谓“床上夫妻床下客”“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这种说教,多年来塞在她耳朵里到处都是,成婚多年,白白浪费了许多青春美貌,他却没有享受多少。碍于梅雪嫣娘家的势力和名望,他也只能听之任之。而另外一方面又觉得梅雪嫣还有几分姿色,若要享受齐人之福非她不可。所以一时之间又拿不定主意了。
吴有才盯着梅雪嫣心里冷笑:你何时把我当成过自己的丈夫了?以往我白天碰你一下,说几句荤话,你就板起圣人面孔,讲一个时辰的周公之礼。我念《十香词》给你听,赞你胸前盈盈而绵软,有无限温柔内里藏,你闹着寻死觅活,说我出此下流之言,非正人君子所为。好,今天我就讲究一下给你看看,那你可就死定了。
“这个案子若是让我判,结果可能大相径庭。”吴有才说道:“俗话说在家从夫,出嫁从夫,这也是礼教伦常,这女子显然是错了。白居易虽然诗文做的不错,但判案毕竟还差了那么一点,也是有的。”
“就是就是,女子最重的就是名节,名节可比孝道要重的多了。”绿意说道。
“我也听小姐读书,书上说了:百善孝为先。小姐的娘家就这么一个女儿,老太爷和老夫人还指望小姐养老送终,小姐若是撒手去了,可让他们如何活下去。若是连累的二老都死了,别人又会怎么说县大老爷呀。大老爷爱惜官声,可要仔细想想,谁会真心称赞一个不懂的孝道的大老爷。绿意,你是想要害大老爷吗?”红情突然跪在吴有才脚下叩头说道。
绿意扑上去在红情的脸上抓了五道血痕,说:“死蹄子,转过脸来让我再抓一把,你这个没事儿只知道养汉犯骚的死蹄子。”
陈凡怒道:“大人面前岂容你放肆,她也是丫鬟你也是丫鬟,你凭什么抓她,我看你是有点丧心病狂了吧。”
吴有才和绿意同时脸上变色,正要说话,床上的梅雪嫣忽然打起了摆子,嘴里发出吱吱呜呜的好像狗受了委屈一样的声音,马郎中捶胸顿足的喊道:“糟了糟了,夫人的病情恶化了,恶化了。”
陈凡说道:“大人英明神武,处事明达,可不能学外面那些老学究老腐儒啊,孔老夫子的老婆也未必没见过外人,夫人有时候还出去逛街呢。怎么偏偏就对大夫防范的这么严密,小的不才,不忍心看着大老爷没了夫人这样的贤妻,少了个斟茶倒水嘘寒问暖的枕边良人,所以恳请大人,赶紧让大夫救治夫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