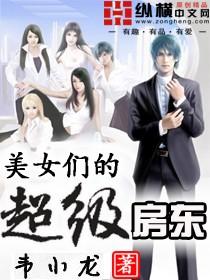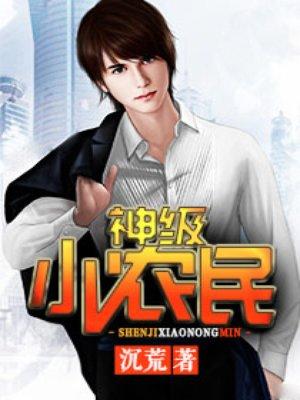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冒牌太妃宠冠六宫免费阅读秦盈盈 > 第210页(第2页)
第210页(第2页)
荣王跪在暖榻前,眼中闪过一丝狠色,“有何不可?在母后心目中,儿臣比不过皇兄也就算了,难道连赵呈翊那个小兔崽子也比不上吗?当初若不是儿臣看他可怜护着他,他早不知道饿死冻死在哪个犄角旮旯了!”
“你还知道他姓赵?你还敢提你皇兄?”太皇太后狠狠地拍了荣王一巴掌,“若是列祖列宗知道你今日所为,看他们不扒了你的皮。”
母子两个争辩一番,最后还是荣王服了软。
他还指望着太皇太后保他一命。
太皇太后自然要保他,不仅仅因为他是她骨肉,还为了皇家的颜面。
赵轩可以不管不顾,她却不行。她不能让百姓和后世议论,说她和英宗养出一个残害学子的儿子。
为今之计,只能找个替罪羊。
赵轩千防万防,还是没防住,礼部侍郎、此次恩科的主考官闫文举在大理寺监牢自缢而死,死前写下血书,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并声称此事系他一力主导,与旁人无关。
赵轩罕见地露出气极败坏的模样,“皇祖母动用了飞龙卫,那是英宗留给她的,本应拱卫龙亭,匡扶正统,却被她用来杀人灭口!”
秦盈盈抓住他的手,不知道该如何安慰。
这些天她陪在赵轩身边,亲眼看着他为了这次恩科不眠不休、殚精竭虑,如今落得这般结果,如果换成她,早就气得把宝慈宫和荣王府都给砸了。
当然,赵轩并不是软弱,只是顾全大局。
事到如今,大可不必了。
赵轩决定把事情闹大,只有闹大了,才瞒不住、压不下,才能让真正的幕后黑手付出代价。
闫大人死后的第二天,上千考生齐聚宣德门,怒敲登闻鼓。
赵轩假称身体不适,没有临朝,考生们便轮换着,整整敲了一天一夜。
激昂的鼓声响彻皇城,全汴京的百姓都出来围观,很快所有人都知道了。
往来的行商、各地的举子或口述或写信把这件事散播到洛阳、郑州、应天、大名,甚至秦州、巴楚……仿佛一夜之间,整个大昭都传遍了。
不,不止大昭,太学中不乏大理、波斯、高丽、本州岛来的留学生,这些人又写信传回自己的家乡。
这下,气极败坏的成了荣王,“那小子疯了吗?脸都不要了?”
赵轩确实脸都不要了,他要的是更实际的东西——科举的公平、学子的利益,还有帝王的权威。
他再也不是两年前那个隐忍憋屈的少年了,如今他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与敌人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