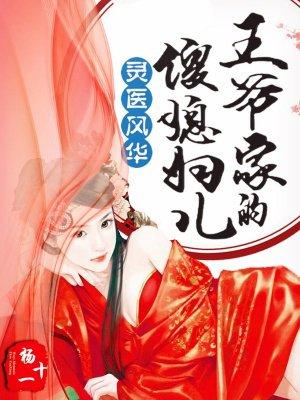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格邓车ao3 > 第24页(第1页)
第24页(第1页)
“谢谢,这是我的荣幸。”盖勒特抱起那本大书,“永别了。”
“等等呀,你就不能给我做个预言吗?”阿丽安娜扒着门框,探头探脑,“求你了,大预言家。你给我做个预言,我就帮你在我哥哥面前说好话。阿不思最听我的,他会对你改变评价。”
“我为什么要让他对我改变评价呢?”盖勒特无所谓地摊开手,“他又不是大人物。而且,即便是大人物,在我眼里,他也不过是——”
偏差了三十厘米,那家伙谁也算不上。
说完,盖勒特上楼回到自己房间,任由巴沙特抱怨和阿丽安娜大声恳求。他施了个闭目塞听,趴在床上看完了球遁鸟戏耍麻瓜的喜剧故事。暮色逐渐笼罩大地,光线渐渐由明转暗。他揉揉眼睛,去厨房抢了个三明治然后上了屋顶。心脏越跳越快,几乎跳出喉咙。“该死的,肯定要发生特别麻烦的事情。”盖勒特嘟囔。两只卜鸟渴望地盯着他手里的三明治,他掏出魔杖,毫不犹豫地炸飞了这种传说中预示死亡的倒霉鸟儿。
他躺在屋顶,试图做出预言,却始终无法集中注意力。过了一会儿,当红霞铺满西方的天幕,他看到阿不福思和阿丽安娜出了门,仔细地别住白色的栅栏。他俩穿着麻瓜的衣服,阿不福思看起来完全是个放羊的野孩子。阿丽安娜则整洁漂亮,麻瓜时兴款式的泡泡袖裙,辫子底下紧紧扎着蝴蝶结,还有一双漂亮的舞鞋。兄妹二人非常开心,哼着歌儿向镇子的方向走去。
“那个阿不思今天不在家?”盖勒特移形换影到客厅,巴沙特正在写信。“对,他今晚可能要回来非常晚……要是十二点还不回来,那就不回来过夜了。加班,魔法部的新章程,重新检查那些考卷。”老妇人推推花镜,“真稀奇,你不是不关心他吗?”
“我看到那个小丫头出去了,还有那个放羊的。”盖勒特给自己倒了杯茶,“该死的,没咖啡吗?”
“注意你的言辞,”巴沙特严厉地瞥他一眼,“我给你伯父写信了,你不能再去德姆斯特朗——好孩子在那里也会变得顽劣不羁,你就是个绝佳的例子,亲爱的。”
“他们出去了。”盖勒特说,茶水滚烫,烫得他差点把茶杯扔出去。“都是卜鸟,”他愤恨地擦了擦嘴唇,“明天我就把它们的巢全烧成灰。”
“今晚有晚会,”巴沙特吹吹羊皮纸上的墨迹,“他们去跳舞了,我猜。”
“跳舞!”盖勒特看了眼壁炉上方的老式挂钟,八点。“他们还是小孩,怎么可以大晚上去外面跳舞?梅林的胡子,我那个年代——”意识到说走了嘴,他赶忙端起茶杯掩饰,“我是说,我伯父从不允许我在这个年纪夜里单独出门,麻瓜的世界充满危险。”
“那是肯定的,盖勒特,你只会在夜里溜出去,把麻瓜当球踢。”巴沙特努努嘴,“不过,确实不安全。阿不思也不许他们去跳舞,大概今天他不在,所以——”
盖勒特重新坐到房檐上,看向镇子的方向。他不知道自己干嘛这样关注阿丽安娜。大概是一百年前的阴影……那个胆怯的女孩了无声息地躺下了,蓝眼睛空洞地睁着。她没有外伤,就像个陶瓷人偶。阿不思抱着这个人偶疯狂地呼唤她的名字,“阿丽安娜,”红发垂落,像一捧血落在阿丽安娜的睡裙上,“阿丽安娜,看看我,看看我——”
“混蛋。”盖勒特闭了闭眼。在遇到阿不思之前和那之后,他遇到过很多死人,也杀死过很多人。他从未感觉到悲伤。清理垃圾有什么可难过的呢?可他为阿丽安娜真实地感到悲伤……也许不是为了那个疯女孩,是因为阿不思。他了解他,知道他的痛苦。他还曾利用过这种痛苦——
九点了。他焦虑地盯着路的尽头。邓布利多家的石屋漆黑一片,阿不思大约还在与魔法部刻板的规章制度作斗争。“我不是为了他。”盖勒特自言自语,“就这一次……”他拿起魔杖低语,“呼神护卫。”
魔杖顶端喷出一丝银色的雾气,没有成型的守护神。他是黑巫师,黑巫师不可能拥有守护神。“呼神护卫。”盖勒特不甘心地试了第二次,他需要守护神帮他寻找阿丽安娜,“呼神护卫!”
银色的雾气越来越稀薄。呼唤守护神需要集中精力回忆,调动起最快乐的记忆。盖勒特悲哀地发现,他在大脑的角落到处搜刮,居然搜刮不到一丝快乐。他的过去——伏地魔、绿光、漆黑的牢房……巧克力蛙,空白的画片……寄不出去的信……阿不思冷静地举起魔杖,血浸透了他的袍子……阿不思抱着死去的阿丽安娜哭泣,“为什么?”他用含泪的、模糊的蓝眼睛望向他,“为什么,盖勒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