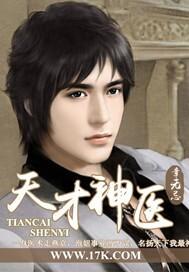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浮图塔番外和原著的区别 > 第53页(第1页)
第53页(第1页)
曹春盎奇道:&ldo;干爹自己不留些么?&rdo;他拧着眉头剜他一眼,&ldo;你何尝看见我擦过粉?&rdo;曹春盎讪讪的,心道也是,何郎傅粉都未必有他干爹这么好的皮色,那些东西对他来说无用,雕琢了反而掩盖了他本来的姿容,画蛇添足罢了。遂弓腰应个是,&ldo;那儿子这就叫人送过去。&rdo;他嗯了声,想起来有些话要交代音楼,也不多言,自己过跨院去了。游廊窄而长,弯弯曲曲多少回转。经过步步锦槅心的槛窗往里看,园子里两个下人提桶跟着,音楼正拿毛竹做的长柄水呈浇花。也不知怎么那么巧,明明离得很远,一抬眼视线碰个正着,她抿嘴嫣然一笑,撂了手里东西往院子中路的青石道上迎过来。他快步进月洞门,两边站班儿的太监对他行礼他也置若罔闻,走近了冲她揖手,&ldo;西向的日头,娘娘不怕晒着么?&rdo;她掖了掖脸,视线在他眉眼间流转,和声问:&ldo;厂臣进宫怎么样?皇上有没有为难你?&rdo;倒叫她猜了个大概,发难是一宗,晚间要来才是个难题。他转身替她挡住了日光,故作轻松道:&ldo;为难倒也算不上,不过缴了臣披红的权,臣总算可以轻省些日子了。&rdo;他说不算坏事,她似乎不大相信,仍旧眯着眼打量他,&ldo;我倒觉得,情愿放弃提督东厂的差事,也比罢免司礼监批红的权来得好。&rdo;他眼里有笑意,背着手道:&ldo;娘娘此话怎讲?&rdo;&ldo;内阁的票拟不再经厂臣的手,你不害怕么?&rdo;还是变着方儿的说他坏事做绝吧!没看出来,她也是个口风犀利的人,先前低估了她,只当她傻乎乎什么都不明白。他叹了口气道:&ldo;是啊,娘娘说得没错,皇上当时收权,臣心里是不大受用。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臣原本是糙芥子一样的人,得先皇器重才有今天,不说主子封赏的东西,就连人都是主子的,自己心里明白,还有什么可不平的?&rdo;她淡淡地笑,&ldo;厂臣这么想是好事,该是你的,你就是虚拢着十指捧也一分不会少。我瞧厂臣一直以来辛苦,有个时机歇一歇,也不是坏事。&rdo;&ldo;娘娘说得是。&rdo;他呵了呵腰道,&ldo;皇上做这个决定在臣意料之内,所以下令的时候并不觉得突然。早前臣和娘娘提起过南下的打算,刚才进宫向上奏请,连带着替娘娘表了个愿,万岁爷也首肯了。&rdo;音楼大喜过望,肖铎的形象在她眼里一下子又拔高许多。他是有把握的人,真如他说的那样,只要愿意,没有一样干不成的。别人提起他的名号,都不那么待见,她却结结实实感激他,悄悄伸手牵了牵他的衣袖道:&ldo;好话我也不会说,厂臣对我的恩情,我怕是没有能力来报答。&rdo;&ldo;这是打算撂挑子赖账么?&rdo;他低头看那纤纤五指落在他的云头袖襕上,笑道,&ldo;咱们打交道那天起我就对娘娘直言不讳,娘娘他日得了荣宠不忘记臣的好处就足了。臣可不是什么良善人,您尊养在我府里,看不见我做的那些坏事,要是哪天见了,只怕对臣再也亲近不起来了。&rdo;她翣着大眼睛看他,&ldo;我听说东厂的酷刑骇人听闻,都是厂臣想出来的?&rdo;他摇头说不是,&ldo;东厂成立有一百多年了,历史只比大邺短了几十年。厂卫杀人名目繁多,什么梳洗、剥皮、站重枷,全都是前辈们的法子。臣接手后无甚建树,不过略略改进一些,娘娘这么问,实在是太看得起微臣了。&rdo;音楼听了大惑不解,&ldo;东厂真是个奇怪的地方,下了大狱的人还能梳洗打扮。&rdo;他仰唇笑道:&ldo;娘娘会错意了,东厂的酷刑爱取文邹邹的名字,比方鼠弹筝、燕儿飞、梨花带雨……梳洗是拿滚水浇在身上,浇完了用铁刷刷皮ròu,直到ròu尽骨露,这个人就废了。&rdo;他轻描淡写,并没有表述得多详尽,音楼却听得骇然,惊惶捂住了嘴,吓得愕在那里。青天白日下明明是那么个温雅的人,说出来的话却叫人汗毛林立。她有些难以置信,难怪世人提起东厂和锦衣卫都谈虎色变,她看见的似乎只有他的好,却忘了他是以什么谋生的。他和她并肩散步,分花拂柳而行,见她不说话了,转过脸来看她,&ldo;臣吓着娘娘了?&rdo;她嗫嚅了下,&ldo;有一点。&rdo;他嘴角微沉,语气无奈:&ldo;这些手段是用来对付触犯了律法的人,娘娘一不作奸犯科,二不贪赃枉法,有什么可怕的?再说臣在这里,就算您害尽天下人,有臣给您撑腰,娘娘自当有恃无恐。&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