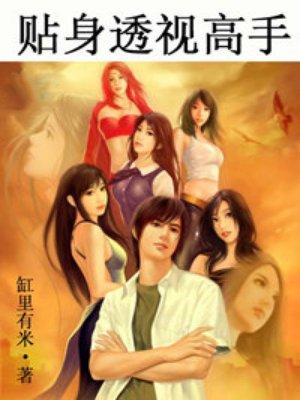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阳光殡葬是什么 > 第二章 手术之日堪回首(第1页)
第二章 手术之日堪回首(第1页)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九号天气不记得了
其实我写这篇日志的时候,已经是十二月的二十一号,所以不记得十九号的天气,只记得那天我睡到9点,朦胧中被人拉起来,在我屁股上打了一针“安定”。然后在护士的搀扶下,来到了5楼手术室,这一层是个好地方,手术室旁边是个全封闭的神秘科室,上书三个硕大的英文字母“ICU”,我作为25岁的资深老病友一看就知道这是传说中的“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ntensiveCareUnit)”,如果我手术时发生麻醉意外或者大出血导致休克,那我就会被送到那里面去……
手术室就是个瘆人的所在,我就不作赘述了。爬上手术台后,有个医生问地上的旧拖鞋是谁的,我说是我的,然后他就把那拖鞋踢出去,说手术室必须是无菌环境,我也只好听他的,但总觉得这好像预示着我这次手术后不用穿鞋了,直接被抬出去……
麻醉医生在我手上扎了个输液,我心想这下可以安心睡一觉,醒来手术就已经结束了。谁知道过了两分钟,我还没睡着,难道麻药对我已经无效了?就问医生:“这不是静脉全身麻醉??”
“急什么,手术医生都还没来,这只是普通点滴而已。”
我无奈,梁主任他们会不会是去吃早餐了?然后打着饱嗝进来给我开刀。几分钟后医生们进来了,我又紧张起来,突然听到有个男护工说:“哟,梁主任这次亲自主刀啊!”我的心情又放松了一些,这医院对我还真重视,主任刀下死,做鬼也叉叉啊!
病友们总喜欢慕名去什么医科大附院之类的大医院,殊不知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首先,病号一多,医疗资源就紧张了,住院两个星期还不一定能开刀,如果是高度恶性肿瘤,估计都开始扩散转移了;其次,病人觉得会有牛逼医生给他们治疗,心里有保障,其实你被全麻之后,你知道是谁给你做手术?在医科大的手术室经常挤着十几个医生,我以为是专家会诊,谁知道是一个主任兼教授领着十几个研究生,而我成了给他们上课的活教材……
梁主任说:“这个病例比较特殊,在我们医院都比较少见,两年不到就复发三次,比普通癌症复发还快。我来开刀,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早已感动的热泪盈眶,主任不仅德高望重、医术高超,更可贵的是还保持着如此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在医疗事业被医疗改革整得面目全非的今天,竟然还有这样纯粹的医者,来吧,主任,使劲割吧!
“主任,这次请割得宽一些,把周围看起来不正常的肌肉也一起割了。”我恳求道,把希望都压在了主任身上。
“好,好,我们尽量割干净,不让它复发。”主任此时高尚得堪比白求恩大夫,我看不到他身上有一丝地基趣味。
主任说:“可以麻醉了,覃姐。”
“但是病人说想要全麻,如果把他翻过来开刀,要插氧气管哦。”麻醉医生说。
“那就搞个半身麻醉好了,搞什么全麻吗?”梁主任不解。
“不,不,主任,是我要求全麻的,我不想在手术时留有意识,太恐怖了!”我说话都发抖了。
“别紧张,我们绝对不会让你感觉到一点疼痛的。”梁主任安抚道。
出于对主任的信任,我竟然同意了半身麻醉。信任别人总是要付出代价的,麻醉医生叫我把腰弯拱成龙虾状,然后向脊椎内注射麻药。我一想到有个大针筒刺进我脊椎,我就不由自主的颤抖,不知道诸位是否感同身受?
医生说:“不要怕,把腰弄弯一点,你看你,紧张得后背都僵硬了,我们怎么扎针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针扎在了脊椎上,原来只是两根细小的银针而已,不算太疼。妈的,我还以为是那种兽医用的那种大针筒,搞得我一直不敢回头看,吓死我了……
随后我感觉后背一阵清凉,怎么说呢,就像是有一股冰冻农夫山泉从皮肤下流过的那种感觉。我被翻了过来,任人宰割,我听到了“啪啪啪”的声音,是电刀!但奇怪的是,我真的感觉不到疼痛,梁主任没骗我,哈哈,脊椎麻醉真美妙!
原来真的有可以在保持清醒的情况下又能彻底消除疼痛的麻醉方法存在,而且这次手术比较静穆,不像上次在医科大热闹得如吃巴蜀火锅一般,我渐渐放松下来,趴在手术台上感受着又一颗肿瘤离我而去……
席间只有一个护工说了句:“隔壁手术室里那个病人真搞笑,又有肝Ca又有HIV……”
我听后差点笑出声来,尼玛的肝癌加艾滋病,这不是双保险死亡判决书吗!还做个毛手术啊?趁着还能动,散尽千金出去快活才是(顺便用HIV报复一下社会哈哈)。估计他也是这么想:得了肝癌之后,拼命出去享受人生,还抱着为人类多消灭一些病毒的崇高理想,在被送进焚化炉之前,把癌细胞、艾滋病、梅毒、淋病、湿疣全都凑齐,来个同归于尽……
意识流让我把注意力转移到别人的痛苦上,我的痛苦就被忽略了,和隔壁那位爷相比,我所承受的简直微不足道嘛!不知不觉,手术已结束……医生把一个不锈钢碗放到我面前:“李左车,这是从你背后割出来的肿瘤,这次是三个肿瘤连在一起切除,还有一些可能被感染的肌肉和皮肤组织,也一起帮你割了,现在我们要拿去化验。”我看着碗里那个像猪脑一样的东东,嘴角泛起一丝微笑:这玩意在我的体内产量真高啊,要是能卖钱就好了……
医生们把我推出了手术区(这次还是没有进ICU)。我看见阿莎在门外长舒一口气,也许她的压力比我还大,我进了手术室之后,她就要随时做好通知我妈的准备:“喂,妈妈,你儿子没了……”
回到8号床之后,医生马上给我接好心电图、氧气管、血压器,实行二级护理,但我的身体开始发抖,原因只有自己明白:我是低血糖,手术之前又不能进食,术后被放了这么多血,导致体温降低,故尔发抖。阿莎、医生、病友全都以为我是太紧张,都在安慰我不要怕,但我当时抖得连发音都有困难,拼命挤出三个字:“水,热水……”
阿莎说:“医生说8小时内不能喝水。”
我说:“暖手……”
她用两个矿泉水瓶装上热水放在我左右手,一分钟后,我就不抖了,脸上也开始恢复血色。
“好了,好了,你看他眼睛这么有神,不会有事的。”病友及其家属安慰完阿莎,停止了围观,悻悻离去。
大约下午四点左右(手术约在十点半结束),我在阿莎的协助下,莅临卫生间,完成了手术后第一次小便,我想申请“全球手术后最快小便的癌症患者”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