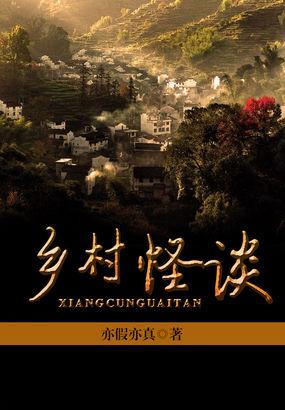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龙门飞甲之化棠曲番外 > 第一百二十六章 共襄举(第1页)
第一百二十六章 共襄举(第1页)
这话听来似是讽刺,自讽,或嘲讽,犹未能知。
顾少棠心思微敛,想问他们和雨化田有何瓜葛,一时竟问不出,也知不是时候。
想着只道:“现下你们是准备要混入王城了?”
天枢想道:“现已耽误多时,须得立刻行动……王城守备森严,还需万事小心,天权,天玑,天璇,你们和我一同行动……开阳玉衡,你们在此留侯。”
“什么?!”
这两孩子一个激灵,全蹦了起来,连声抗议——
“这怎么可以?!”
天枢手掌伸出,按住开阳脑袋,觉他安静下来,才沉声道:“行牒只有五份。”
开阳完全无法认同:“既有五份,我便当去!都是血海深仇,我怎能袖手旁观!你们去犯险,我又怎么坐得住?再者你说我已将这九州穿云弓用至化境,为何总不让我一显身手?!”
他这情绪激动的,深怕他不许。
玉衡自知抢不过开阳,也还是要争取:“天枢,我……我也想去,我会帮忙,也会保护自己,绝不会拖累你们的……还有……我……”
那些任性的话,她自知不能再说出口,咬住唇心中难过。
她想见一见如今已变成乌兰图娅的摇光,不把她找回来,她总不会死心的。
顾少棠见开阳闹得愈凶,动静颇大,处理不好自己是要讨嫌,寻思着只招手道:“我这既然是个没在计划里的外人,也不好抢了你们的份,我那一份行牒便不要了。”
开阳闻言,壮了底气,讨得更是大声。
天枢略略偏首,有些疑问。
顾少棠向他道:“我瞧这两个跟我脾气挺像,说不许去,偏就要去,不盯着恐怕要出事,不如分头行事,你们带这孩子进去。”她指指开阳,又拉过玉衡来:“这孩子我来带。”
玉衡讶然看她,因不相熟,满是懵懂。
天枢默然一刻,疑道:“你打算如何进去?”
顾少棠莞尔一笑:“我自有办法。”
————————
日耀尘嚣,水濯鸿宇。
王城之内,宫殿四落,青瓦粉墙,旷地铺展。
柏梁宫门户大敞,殿宇宽阔,殿外白石阶向下叠展,接住石板道,长长蔓延而出,唯见两旁各植一局菩提巨树,正对着一座破败半颓的佛塔,而寝殿之中,帐幔低垂,锦缎垂穗,正荡出欢爱声响,不闻男子喘息之声,只有女子婉转吟哦,**不断。
案边残酒,犹存“七夜明媚”的气息,杯沿有秾艳的胭脂色。
雨化田端身坐在案前锦裀上,沉目思索,充耳不闻,姿态宛如礼佛。日光从外投入,将他的身影长长拉扯,光明射不进他心里,脑海之中,只有背后那一座佛塔倾颓,颓到一片黑暗里,埋入深渊之中。
佛塔森森闭着门,残破的窗棂筛入一阵模糊的光,照不见残破佛像上干涸成褐的鲜血,机关构件散落一地,尘埃里只有死亡阴沉沉的气息不断翩跹起舞,他的鲜血早已干涸凝痂,筋肉被虫蛆侵蚀见骨,佛塔成了他的灵柩,却还没有机会得到安葬。
垂帐之内,声响不断。
胡姬的呻吟从千娇百媚渐至惶惑不解,最终化为恐惧中发出的模糊低喘再到戛然无声。
君王帐暖,不过又一个玉殒香消。
近身侍儿低眉垂眼,将垂帐左右揭开,俟那人衣裳未整慵懒走出,便去收拾残局。
床沿鲜血颓淌。
羽奴思矞袍未束,覆肩而裸裎胸膛,曳地瑟瑟而动,裹着森然气息,沉步越过雨化田身侧,目光慵沉沉临窗看向佛塔:“你想沉默到几时?”
雨化田不予理会。
羽奴思偏首而向,鹰目狭长,沉沉将他睨视。
归得西域来,雨化田未再束发加冠,鸦鬓两束,集于背后,贯以白玉骨珠为饰,汇入黑瀑般的长发,披背迤地,衬得昳丽无双,而只这一身玄银相间的雁羽纹阔袖黑袍束腰齐整,更端得丰神俊朗。
羽奴思陡然探手而出,睐目冷然:“焉能怪我?限你月内归来,你竟敢避而不见?”
雨化田下颌被迫抬起,凤目微开,眸中尽是冷然。
羽奴思俯身将面孔逼近,阴沉与他对视,冷冷吐言:“别忘了辛眺之死,是你下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