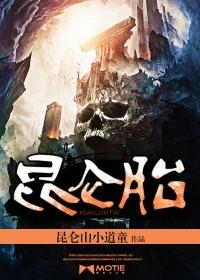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骑鹿难 > 041-治水开封-1(第1页)
041-治水开封-1(第1页)
话说中秋节前几日,河南布政司告破一起大案,震惊朝廷。
一月前,黄河流经中原一段由于连日大雨,数处河堤决口,仅洛阳至开封便有两三处之多。一时间河水泛滥,冲毁农田房舍不计其数。如此严重的水患几十年难遇,仅凭此事河南布政使及下属督河官员便要判上失职之罪。岂知按查使一纸奏章速送刑部,状告布政使多年来私敛民财,克扣河防征银,贪赃近百万两白银。河南自古便是黄河多灾之地,一旦河防疏漏,大水来时一发不可收拾。刑部不敢怠慢,急奏圣上,顿时龙颜大怒,下令吏部尚书王文赴河南查办此事。不到一个月时间已查获赃银八十五万七千余两,两名布政使招供属实,于是朝廷派军队将二人押解回京交刑部听候发落。
封疆大吏贪赃枉法屡见不鲜,但大都将财物分藏密处,如此轻而易举便水落石出不免让久经官场的人觉得蹊跷。数位官员建议刑部尚书对此案再审。谁知,隔日宫中便有敕下将二人送诏狱。而就在九月初六将要堂审的前一天深夜,两名布政使在诏狱中畏罪自杀。狱吏说睡着了没看见。验尸官见两人均为头颅破裂,墙上满是血迹,便验定了确是自杀,于是河南一案就算了结。然而,黄河决堤尚未修复,江西饥荒,沿海倭寇又现猖獗之势,当政大员们寝食难安。
初八清晨,五更过后,百官于朝房内外等候上朝。皇帝御体欠安,已罢朝两日,听司礼大太监曹公公说,皇帝中秋赏月,略感风寒,看来今日临朝的机会不大。所有官员已陆陆续续地进入午门,朝房外的走廊上站满了人。河南一案成为众官员近日津津乐道的话题。布政使在诏狱触墙自尽,不少人都明白是锦衣卫做下的,但没人敢在大庭广众中随意猜测。这天正巧樊瑛当班,于是站在一旁不动声色地听着,身为北镇抚司的千户,他当然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两名布政使若早有自杀的念头,又何必待到现在。可假造现场的指令是谁下的呢?他看了看不远处的指挥使朱骧,此人尚且忠厚,不会做此等事。又想到了自己以前的顶头上司门达,如果是他倒还有可能。锦衣卫衙门里头不经指挥使便能下令的就只有东厂厂公曹吉祥。曹吉祥在北镇府司里头倒有数个亲信。一想到曹公公和他的亲信,樊瑛横竖不是滋味。北镇抚司千户,名义上是圣上直接管辖,但圣上口谕都由曹公公传达,来去之间,不知有多少消息被曹公公隐瞒。东厂行径世人皆知,而像他这种锦衣卫只能不明不白地背黑锅。朝中大员大都惧他三分,只有武清侯石亨同他交好。
这时廊外有人相互打招呼,樊瑛回头一看,是吏部尚书王文。樊瑛忽然主意一闪,走上前去向王大人作揖道:“王大人此行河南,劳苦功高,下官没有早日道贺,实在过意不去。”王大人微笑道:“樊大人不必这么客气。”樊瑛恭敬地请王大人进入偏厅,见左右无人,小声道:“王大人,请教一事,有关河南一案,大人以为二位自尽的布政使,在交待贪赃银两时,其态度如何?”王大人徘徊两步,道:“供认不讳。”樊瑛轻轻一皱眉头,又问:“那藏匿的赃银查找起来可还顺当?”王文道:“既然都招供了,不怕找不到。”说罢看着樊瑛的脸道:“想必这事樊千户了解得比我多,我也不用再说了。”转身向另一间厅中找于兵部去了。
于谦正和工部江尚书对坐喝茶,见王文前来,立刻看茶。于尚书和江尚书各为公事烦恼。黄河堤坝由于钱粮缺乏,河工连日劳顿,加之阴雨连绵,决口处的修筑一直耽搁着,如今又下了两个布政使,看来又要派御史救急了。江浙福建倭患严重,急需军火,不仅河运漕运全部用来运火药粮饷,一部分赈灾的官银也拨与军用,灾民日增,盗贼见多。这次收缴的赃银的确派了大用处。一些内阁大臣们都觉得多事之秋即将结束,户部尚书李琦和几位宗人府的老头儿商议年底俸禄奖赏的分支。
不一会儿已是五更三点,还是没听见击鼓鸣钟,看来皇帝仍在病中。这时曹公公掌着把拂尘,目无旁人地走进朝房大厅内,环顾一下,不紧不慢地道:“龙体欠安,今日罢朝。”说完便要走。江尚书赶紧走上前道:“曹公公且慢,我这里有份急奏,烦劳你转交圣上。”从袖口拿出折子,递与曹公公。曹吉祥展开一看,点头道:“江大人宽心,圣上无甚大恙,我会替你转承的。”将奏折塞入袖中,不理他人,只和石侯爷一笑便出去了。百官相互道别后纷纷回衙门。
石亨与樊瑛一同走出皇城,待左右无人之际,石亨轻声问道:“自杀的事是东厂在捣鬼么?”樊瑛道:“我也没查清楚。不过,看来为了治黄河,朝廷还会派人上河南,不知指派的是谁。”
江尚书的奏折正是请皇帝派遣治河御史赴河南,督修河防。这皇帝一生病,事情不知会拖到何时,江尚书心急如焚。但这回可巧,圣谕隔天便下来了。
十日一早,曹公公的亲信,司礼太监郭喜风风火火地走进了工部大院,江尚书连忙出厅相迎。郭公公手捧圣谕,身后带着十多名随从,大模大样步入正厅,说道:“督水司员外郎丘大人可在?”江尚书一愣,随后忙吩咐左右道:“还不快去叫丘大人出来。”一名小吏立刻拎起袍襟跑了进去。
丘胤明正与几位主事一道整理各地官员上送的信件。老郎中大人手持一块琉璃镜片,埋头看信并不时地做着笔录。忽然有人奔进来,高声道:“郭公公奉旨前来,要见丘大人。”所有人都抬起头来,十几只眼睛齐刷刷地望向一脸惊讶的丘胤明。小吏又道:“看郭公公的脸色,丘大人看来要交好运了。”丘胤明没有时间犹豫,赶紧整整乌纱,快步来到正厅,一眼看见江尚书也在,便立向侧边。这时郭公公从椅子上站起,笑着对他道:“丘大人,久闻大名,今日一见,果然人才出众啊。”郭公公的声音又尖又哑,让人听着毛孔发紧,丘胤明低头作礼道:“不敢当,公公驾临,下官有失远迎。”
郭公公笑道:“上回塘沽海防修得真漂亮,圣上有意提拔新秀。”说罢展开金卷,高声说道:“工部督水司员外郎丘胤明接旨!”所有人都跪下来倾听。
“奉天敕命,皇帝敕曰:今河南水灾,伤田毁林,流民隐患不可轻之。河决开封,久治不愈,若长此以往,劳民费财将伤国本。现命工部督水司员外郎丘胤明为治河佥都御史,即日赴开封府整治河防,安抚灾民。钦此。”
丘胤明谢恩,接过圣谕站起身。他真不明白皇帝怎么单单挑中自己。这不是一桩容易的差事。郭公公事不关己地道:“丘大人,赶快启程吧。”带着随从拂袖而去。丘胤明无话,匆匆告别江大人回家去。这下工部里头议论开了,大都都不清楚这是谁的主意,有人说是曹公公,有人说是于尚书,还有人说是江尚书。倘若这丘胤明真能把河南的水患治好了,便是前途无量。可钦差河南从不是件容易的事,黄河大水屡治屡犯,是朝廷的一大心病。
话说丘胤明走到家门口,见樊瑛的大红马在门外,便知他已在里面。果然刚踏进门槛,柴管家一路小跑地出来,老远便道:“大人,樊大人在书房里等你呢。”丘胤明点头道:“我明日要去开封府,你去帮我打点一下衣物。”柴班好奇道:“大人这回是……?”丘胤明道:“治理黄河。大概要去些时日了。”说完径直向书房走去。
推开房门,只见樊瑛坐在窗口的椅子上喝茶。樊瑛见他进来,起身笑道:“承显,才回来。我昨晚听说你被指为御史,所以一早就来找你。”两人就座,丘胤明道:“我做御史,一定成了朝廷里的新鲜事。想必正南兄知道此中一些原委。”樊瑛道:“看来你还不了解当今朝廷的真面目吧。”丘胤明摇头道:“兄长见笑了,我确实还没有这个机会。”樊瑛笑道:“你快要平步青云了。知道是谁举荐你的?”未待丘胤明说话,樊瑛继续道:“曹公公。”
樊瑛一脸认真地说道:“现在朝廷百官,凡是懂得利害关系的,或真或假都要找个靠山,那便是石侯爷和曹公公。曹公公虽是太监,可总督京城大营,还掌握着东厂,谁不惧他?只有石侯爷手握兵权,才能与之并肩。于尚书虽然深得圣上的信任,可是他清高无比,鲜有人与他交好。”
听他这么说,丘胤明也明白,皇帝身体虚弱,朝廷里的生杀大权定是落于石,曹二人之手,于是便道:“那,兄长是站在石侯爷一边了。”
樊瑛不置可否,只道:“曹公公为人阴险,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若论真心,我只佩服于大人。当年太上皇被瓦剌人俘去,也先大兵进攻京师,多亏了于大人竭力主战,用人有方,军民一心,方能大破敌军。我也参加过京师保卫战,亲眼看见于大人敬忠职守,号令众将协力守城。京城百姓都知道他是当今第一刚正廉洁,为国为民的好官。”看见丘胤明若有所思的样子,樊瑛又道:“但朝廷不是江湖,任你一心为国,高风亮节,若得罪权贵,即使是一品大员,稍不留神也会落个死无葬身之地。一人生死事小,可家属亲友却都要无辜遭难。”
丘胤明点头道:“我懂你的意思。曹公公推举我做御史,想必是要试探我,但不知其中有什么奥妙。”
樊瑛道:“知道河南布政使自杀的事吧。我肯定曹公公与这案子有关系。你此去开封府,万一查到什么,若牵涉到曹公公,千万别轻举妄动。我会派人暗中去查访,但你身边一定会有东厂的奸细,我也不知是谁。反正记住我的话,以你现在的身份,是绝不能得罪曹公公的。”
丘胤明道:“兄长对朝廷的生存之道解释得好,不知我何时才能学到这么多。”
“你是个聪明人,”樊瑛笑道,“用不了多久。”说罢盖上茶碗,起身道:“时候不早,我该去衙门了。你若明日一早动身,我就不来送了。你多保重。”
“多谢兄长指教,我不送了。”丘胤明开门目送樊瑛出门。
晚间丘胤明到东方家拜访。祖孙三人听说他被点为治河的御史,十分高兴地向他恭喜了一番,他倒是觉得有些不自然。东方炎与他是同科进士,如今却唯独自己连连升迁。不过东方炎是个心胸宽阔的人,从来不计较这些。丘胤明暗自欣慰。
第二天一早,门外人马喧闹,柴管家兴奋地跑进来道:“大人,原来你这回是钦差呀!”丘胤明道:“家里就请你好生照料了。记得常给马准备好饲料。”
门外已有几十人的队伍等候,邻里左右挤在道旁看热闹,“肃静,回避”的牌子漆得发亮,马车两旁均有骑兵护卫,“治河佥都御史”的青色大旗引人注目。一名随从副使上前道:“大人,请上车。”丘胤明转脸环顾了一下随行的人马,道:“旅途劳顿,有劳众位了。”转身上了马车。坐定后只听铜锣一响,人马浩浩荡荡的上路了。
马车经过京城的闹市,耳边回旋着道旁百姓的议论声,铜锣“哐——哐——”的响着,听不清人们说的是什么。走了许久,四周方才安静下来,他撩起布窗,见已出了广安门,快到卢沟桥了。秋风袭人,满目金黄的草木使人心旷神怡。好些天没有出城遛马了。可眼前该想的是正事。在京城领皇粮也半年多了,民间的景象似乎越来越淡,他忽然感到些许不安,下令收起铜锣,快行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