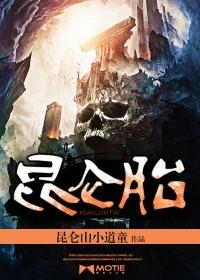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渡灵铺完结了吗 > 第73章 巫山绢与阿魏散十七(第1页)
第73章 巫山绢与阿魏散十七(第1页)
茜素用力抹了一把眼泪,一个劲儿地点头,我冷眼旁观着他二人,心里说不上来什么滋味。
崔清河的目光缓缓移过来,终于落在了我和师傅身上。“朱先生……阿心姑娘……”他讷讷地将我们一个个唤过来,仿佛不敢确定坐在他跟前的人是真实的还是幻象。
睡了这许久,自然是有些呆滞迷蒙,
“朱先生……”崔清河吃力地向师傅探出一臂来,请师傅挪坐于他身旁。“朱先生,我睡了长长的一觉,做了个梦……同真的一样。”
师傅替他把过脉,笑道:“崔公子只是身子有些虚,调养两日自然就好了,余事不必多想。”
崔清河对师傅的话置若罔闻,坚持着自己的念叨:“这梦好生奇怪,说不清是什么事,仿佛并没什么特别,只是与绿艾平平淡淡地过了一世。人这一世真短,不知不觉间就过去了,梦里我仿佛还没好好地看过她,就要离世了……”
“清河,你说什么呢,我不是好好地在这儿么。”茜素蓦地打断他,尴尬地向师傅一笑:“朱先生莫理他,他……大约神智还未全复。”
崔清河的手一把搭在茜素的手腕上,睁大双眼,仔仔细细地瞧她,瞧了片时,古怪地笑了笑:“绿艾,你与我梦中的你,甚是不同。我醒来后,竟,竟有些不认得你了。”
茜素的脸蹭地一下变了色,“清河……清河,你,你睡糊涂了么?”
“你也不必逼他,此事急不来,须得慢慢调回。”师傅劝道,算是替他们打了个圆场。“若无旁的什么事,还烦请娘子将药资结算结算。”
茜素将脸上的残泪擦拭干净,站起身来将师傅往一旁的席案引:“药资自然要结的,朱心堂的规矩我也听过一二,敢问朱先生要如何结算药资?”
“我这阿魏散得来不容易,药资么,还望娘子不要推脱。”师傅倒也不同她客套,径直道。我暗自赞同,这药果然是得来不易,幽都都走了一遭,寻常医家哪里能拿得出这样的药。
茜素肯定地点点头:“朱先生只管说,便是要我这条性命,也绝无二话。”
“娘子言重了,我要你的性命做什么用?”师傅摆手笑道:“我只要娘子的一幅画像。”
“画像?”茜素双眼避开师傅的目光,偏到一旁。“画像能值什么?况且……若是别的什么画便罢了,可这画像,毕竟是闺中之物,是不是有些,不合宜?”
师傅竟教她驳得无话可回,只得拱手歉然道:“对不住,在下一向推崇茜素姑娘的画作,而今,茜素姑娘她……再想得一幅便是万难了,故有这番索求,到底是唐突了,对不住。”
茜素松了松眉头,飘忽的目光也定住了,她稍加沉吟,便道:“难得朱先生垂青我阿姊的画作,我这儿尚有一幅,虽抵充不了药资的一二,先生若是不嫌,便拿去赏玩罢。”
说罢她转身往柜子去取画,我听着她说话的口吻,心里断定她就是茜素,决计错不了。
茜素捧着一卷画轴转回来,双手递到师傅跟前。
师傅接过画,展开卷轴来看,我凑过去望了一眼,正是那只不知所踪的玳瑁大猫。画中的猫儿无论是熠熠的目珠,还是分毫毕现的细毛,都与真猫无异。
“茜素姑娘的画作,真真是灵性。”师傅轻抚着作画的绢帛,喟叹道。我知道他一定肯收下这幅画,因为那作画的绢帛,也是一方巫山绢,流落在外难免再惹祸。
果然不出我所料,师傅收好了画,带着我告辞,临行又嘱咐了崔清河几句,要他宽心补养,莫作他想。
待出了崔家的门,我回头望望崔家那体面却陈旧的大门前已没了茜素身影,这才问师傅:“崔家那个定然是茜素,不会有错,还有那幅绿艾的画像,还在崔家,师傅就不理会了么?”
师傅显出极少见的无奈,蹙眉道:“自然不能不理会,可那茜素心思甚重,我若强要,恐她有所警觉,她又不知巫山绢的脾性,倘就此毁了画像……”他话不肯说完,只是摇头,随后又拍了拍手里的玳瑁猫像,宽慰自己似地道:“总算收回了一帧,也不算白跑这一遭。”
“她要是真毁了画像,将如何?”我紧张地追问道。
“还能如何,没了便是没了,了无痕迹。”
我心头一跳,惶惶然不敢想下去,一时也想不到有什么法子能将绿艾的画像从她手里收来,确也只能按兵不动。
中元过后铺子冷清下来,师傅遣我去望探过一回姚装池夫妇,顺道打听打听,茜素有无回过姚装池。
一问之下,她果然未曾回过娘家。我依稀记得绿艾说过,因她与茜素的样貌、身段、嗓音都酷肖,鲜少有人能辨得出,可她们的母亲却能辨得分明,茜素心里亏虚,一直借崔清河这一病来推脱,不曾回去见过爷娘。
姚装池的头发几近花白,整个精神垮塌下来,铺子虽还开着,活却做得有一搭没一搭。这个铺子没有绿艾风风火火地穿梭其间,便跟没了魂一般。
姚母卧病在床,我去诊过脉,她自己无法振作起来,药石无用。她拉着我一个劲地说从前茜素如何如何知礼乖顺,而今绿艾成了婚,家中遭逢大不幸,也不肯回来望望,言语中颇多怨怪。我除了写个补气益血的方子,说几句安慰的话,也帮不上她什么。
就此情形,我不敢想他们获知真相后会如何。我忽然觉得茜素虽然行了可恶之事,但她倘或就一直扮演绿艾扮下去,好歹姚装池夫妇不会再受一次重创,崔清河一辈子蒙在鼓里,也可躲过一次摧心肝的剧痛。
我回铺子禀知了师傅,师傅沉默了半晌,吩咐道:“明日咱们再去一回崔家,便说是为回访崔清河病情来的,看看那边的情形再作打算。”
一提到巫山绢这一桩,师傅的眉头便拧到了一处,我再没见过哪一桩能烦扰着他了,此事果真是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