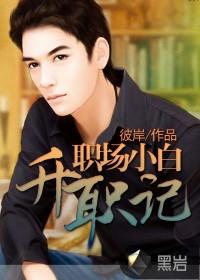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三喜番外txt百度 > 第62页(第1页)
第62页(第1页)
渐渐地,他的影子淡去,另一个人走了进来。他神采飞扬,如同一团烈火,任是走到哪儿,都让人无法移开目光。他手执豪管,挥墨如舞,下笔如神。他时而放声朗笑,时而暴跳如雷,时而强取豪夺,时而深情款款。忽然,他身影消散,我听到风中传来一声小君,忙循声去找,转身却又见到,他跪在灵堂前头。当我碰到他时,他脸色又变,将我一推,说,是不是因为你恨我。他化作红烟消散,我抬起眼,就见到繁华长街,河上莲灯盏盏,一只手蓦地执来。我一见他,就看那目似剪水,人似空谷幽兰。他一手拿着灯,一手握着我的手心,伴我走过长夜。然后,是床榻之前,他神色灰白,两眼通红,一遍遍说,我不甘,我真的不甘。紧跟着,那双眸如若灿星,许诺说,下一辈子,只有我们两个人。他们的身影慢慢消逝,许许多多的人影出现在眼前——“一些不大顺耳的话,我就不说了,沈氏没来得及教好你,而我这个做母亲的,也只好为了儿子,多费些心思。”“四哥儿,你的书都读到哪儿了?”“男人啊,你把他伺候舒服了,他就会疼你、爱你一时。可记住,别把这心给搭进去,若不然,以后疼的,还不是你自个儿。”“四哥儿,快快过来,来试试姨娘给你做的这件新衣衫——”“我反正是个迟早都要死的,你当然要让我!大哥,既然如此,你不如把他也让给我,别跟我这个短命的争!”“她泉下有知,是该知足了,只委屈了我的四哥儿……”“一梳富富贵贵。二梳无病无灾。三梳百岁无忧……”“呸!她以为我真稀罕她用过的东西!”“那下次不管怎么样,你都把他让给我几天,如何?”“四哥儿、四哥儿,要不是因为你,姨娘我早恨不得也跳了井,一了百了!”“今上有意今秋出兵北伐,到时候,我就会带军出征,挥师北上。”“四哥儿,你去了京城,一定要规规矩矩,嘴记得甜一点,别成天跟个闷葫芦一样,啊?”“冬天来了,燕子也要飞走了。”“姨娘这辈子,就指望着四哥儿了,你定要好好儿的,知道么?”“原来,我以为的郎情妾意,举案齐眉,全都是一场笑话!”“记住姨娘的话,四哥儿若是能留在京中沈家,就算是为奴为婢,也别给我回来……!”——别给我回来!“喝!”我猛地大震,两眼睁开来。我发觉,我正趴在冷冰冰的地上,周围黑漆漆的,没有一点光亮透进来。我怔怔地环顾着,隐隐约约,听到了像是一颗珠子坠落到地上的声音。随着珠子滚动的声音,它渐渐近了,最后,就停在了我的双眼之前——那是一颗,红艳如血的珠子。“唰”地一声,我从床上坐了起来。“呼……呼……”我出了身热汗,茫茫一抬眼,看了看周遭,只觉眼前这个地方陌生得很。我摇晃地从床上下来,趿着鞋,轻轻地喊了一声:“姨娘?”无人应我。“姨娘……”我又提声,唤了唤,“三姨娘……”我仍旧没有得到回应,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陡地攀上了我的心头。我突然夺门而出,暗沉深夜,长廊无尽,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起来:“姨娘!三姨娘!”我嘶哑地沿路叫喊着,接着我看到前方一盏一盏的火亮了起来。不知道是谁人唤道:“少君、少君,您怎么回事!啊!”我推开那人,惊恐地跑了出去。“来人!快来人啊!”我一路逃着,不知道自己在何处,也不知道自己要逃到什么地方去。蓦地,我脚下一绊,重重地摔了下来。我喘着粗气,颤颤地抬眼四顾,眼前尽是黑魆魆的一片。这时候,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画面。大哥脸色微变,开口时支支吾吾,好似有什么难言之隐。末了,他似乎明白,不可能瞒得住,便道:“两年前,三姨娘接过你的血衣,也以为,你已经死在京城。”“她不言也不哭,下人也未曾察觉异样。”“五日后,三姨娘就被人发现跳了井,她手里……还抓着你的衣服。”犹记得,府里的下人说,如果能生而为尻,嫁进豪门,全家就能鸡犬升天,一生都不愁吃穿。其实,我一直都以为,三姨娘只恨我不是五妹,给不到她体面。我原本以为,我嫁进了徐家,她总算能扬眉吐气,下半辈子,都有好日子能过。我之所一直都在忍,是因为,我明白,哪怕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也要想一想,我那可怜的母亲……我怔怔地望着,渐渐看清了眼前的景物。乌云蔽月,没有一点光,也没有可以逃脱的地方。“啊!!”我深陷烂泥之中,十指蜷曲,蓦地哽咽地嘶喊,伏地痛哭出声。宁武十年八月十一日,我私逃出徐府。十日后,我在京外渡口,被徐大少爷给亲自擒住,押了回去,关在祠堂里,只等三个少爷都齐了之后,再行审问。xx解释一下,那个红色珠子,就是,三喜在沈家前堂,被检出是尻的时候,从青铜兽嘴里掉出红色的珠子。京外渡口,在我登上船的时候,徐家的人马便恰好赶到。船家怎敢忤逆,正要停船,我仿佛听到了谁的呼唤声:“三喜!”我纵身一跃,跳了江。江水极冷,也极苦,我看着江底,黑黢黢的一片,它又让我想起了,沈家偏院里的那一口井,那里是不是也像这样。极冷、极苦。直到我转醒,静静地看了眼周围,兜兜转转,我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徐家人把我关在祠堂后头的院子里,这个地方,一直是用来关押族中犯下大错、等待发落之人。我虽是被关着,但并未受到苛待,吃穿用度和过往并无多大区别,只除了一个聋哑的下人之外,我就没有再见到任何一人。八天后,徐燕卿归京。那日,天刚亮,我就已经坐在床头。哑奴走进来,伺候我梳洗换衣,之后就领着我,一步步走去了内堂。眼前的一扇门被缓缓地推开,那里头门窗掩蔽,微弱的光透过窗纸,成就一个个斑驳交错的虚影。内堂里,没有徐氏宗伯长辈,也不见徐家老爷和夫人。这里,就只有我和他们。他们三人各坐于三方,不分上首。我走到中央的位置,便执着下摆,两腿分开平伸,挺直脊背,同他们一样,从容地屈膝,跽坐于地。徐燕卿在我的正前方,徐长风位在背着光的东面,徐栖鹤则在西面。阒寂无声。少焉,那低沉喑哑的声音,从我的东面响起:“沈氏敬亭。”我纹丝不动,只轻轻启唇:“是。”“八月十一日,你未告知任何人就离开徐府,整整十日不归,可有此事。”他的声音平如死水,没有一丝波澜。我应了一声:“是。”徐长风又道:“八月二十一日,你在京外渡口,是意欲离京。”我又应:“是。”徐长风问:“所以,你确确是私逃出府。”他静了数息,“你此意,是出自自愿,或是曾受他人撺掇,亦或逼迫。”“我私逃出府,是出自自愿。”我一字一句地说,“不曾受人撺掇,也不曾受人所迫。”几乎是接着我下一句,他问出声:“那你,究竟为何要不辞而别?”四周沉寂了下来。我目视正前,不偏不移,神色淡漠如尘。徐燕卿静默凝视,他原是意气风发,如今静如死水。他开口问:“你坐船,要去什么地方?”“管道易截,水路难追。”我缓缓说,“天下四海,任是到哪一处,都比白白地枉死在这儿好。”我目光虽落在前头,其实却望着远处,就好像这里的一切,已经和我无关。他们,也和我无关了。“你这句话的意思,可是怕……我徐氏将来,会连累了你。”我看着他,遂轻一点头,应了一句:“是。”徐燕卿想是未曾料到,我居然会如此坦荡。“我不信。”他说。闻言,我嘴角轻扬,实在禁不住,笑出了一声。眼前那一双厉眼倏地投来,好似恨不得在我身上凿开一个洞。“众所皆知,徐家如今已是危如累卵,不过是勉强再撑一时罢了。如今,天子病重,怕是已经等不及,迟早会对徐氏动手。三位少爷不见,徐府里的那些下人,暗走的走,暗逃的逃——”我语气平缓道,“我自然,不能不为我自己打算。”徐燕卿定睛看着我,两眼眨也不眨,像是在看一个极其陌生的人。他张了张唇,寒声道:“滴水之恩,当泉涌相报,这些年,徐氏予你身份地位,富贵荣华,不曾短过你一分一毫。即便,是真有那么一日,你真以为,我们三个人,会眼睁睁地看着你无辜受累……”徐燕卿似在强作隐忍,可双手已颤颤攥成了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