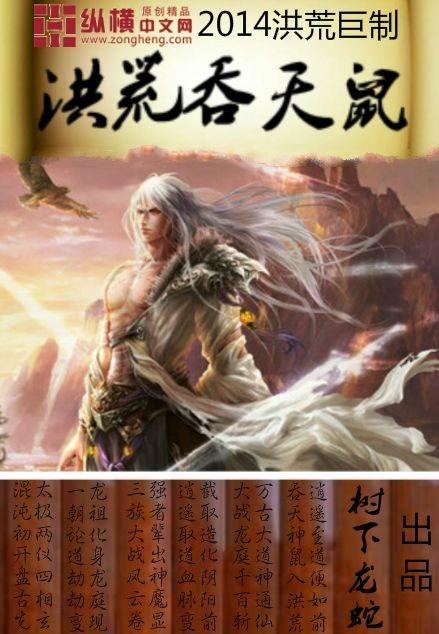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赌棍天子 百度 > 第174章 鹿血酒(第2页)
第174章 鹿血酒(第2页)
杨寄心道:叱罗杜文脑子被门夹了,才想着去攻雍州!雍州夹在凉州和豫州、荆州之间,若是三边包抄,雍州就算打下来也不能长久。何况又是黄河边的防务,北燕素来是弱项,为何要自曝其短?他扬眉欲要发言,突然听见沈岭的一声咳嗽,心头一凛,闭了嘴。
皇甫衮拧着眉头,沉默了半晌,又自己说:“此刻,少不得从权了!杨将军,只能请你牺牲了,凉州调兵的虎符,交给太傅处置吧。朕现在就传旨命太傅都督凉州、雍州、荆州三处,便宜从事。”
好!原来要他杨寄的地盘和人。杨寄老大不愿意,低着头撮牙花子不说话。皇甫衮催了两声,杨寄才抬头说:“凉州兵,原是我西府兵和北府兵里带去的,北府军大半是贼囚徒,还有些是北燕的俘虏。麻烦惯了的,旁人治不治得住我不大清楚。”
坐在一旁的皇甫道知冷冷道:“这个时候,治不住也得治了,杨将军怎么不懂呢?”
杨寄立刻明白了,这不是和皇甫衮上次对他说的计划一样么?叫他杨寄的人阳奉阴违,折腾死庾含章,夺回朝中庾姓的大权才是真!好一个一石二鸟!他想驳回,但燥热得稀里糊涂,不知怎么说好,只觉得脑门子上一直在出汗,忍不住拿袖子擦了擦。
皇甫衮见杨寄不言语了,便道:“若是太傅都督三州事务,势必无力监管原本扬州刺史的事务。而扬州刺史责任至重,扬州十县,几乎包含了天下粮仓之地,军需后勤的补给全数在此,不能稍有疏忽。众卿觉得,这个职务谁担任合适呢?”
这样重要的职务,为何赶在这半夜三更的非处置不可?下头一片窃窃私语。这时,他身后文官班列里,何道省踏出一步,举笏板道:“臣以为,既然杨将军让出西北三州的军权,倒不妨把扬州刺史的位置,给杨将军兼领。”
杨寄心头一“咯噔”,迅速地瞄了瞄皇甫衮的神色,然后低下头装傻充愣学哑巴。
皇甫衮忍不住地色变,摇摇头说:“不大好吧。”
皇甫道知亦说:“杨将军毕竟没有处置民政的经验。”他意满踌躇地望了望侄子,等着这个好位置按原先所说的,落到自己的头上。
没成想皇甫衮却道:“皇叔所言极是。杨将军定不会为区区刺史之职与国算计。扬州刺史的职位,朕思来想去,既要有能,还需有闲,皇叔本来倒是有檠天架海的能耐,只是中书令职位紧要,万不能分心。所以,只能先叫朕最信赖的黄门总管徐念海来担纲了。”
明堂下头“窸窸窣窣”一片私语声,反对的意思明显,与大哗也差不了多少。皇甫道知脸色青白僵硬,着意看了看杨寄。杨寄倒是顺着其他人的目光,看了看皇甫衮身后站的那名老宦官——一直不动声色出谋划策的他,今日终于忍不住要来抢位置了!
“臣期期以为不可!”何道省横眉怒目,站出来说。杨寄却知道这样的紧要位置,这会儿硬争根本没有结果,何道省不必把自己栽进去拔不出来,因而发言阻止他道:“何郎中,陛下令下,臣等遵旨便是。”
皇甫衮见杨寄帮衬,到底还是少年人的心性,得意地挥退了大家,满脸遏制着笑容,却遏制不住眸子里的笑意——根本不像刚刚听到敌人侵袭的紧急军报。
大家默默退散,沈岭在无人的地方,暗暗给杨寄竖了个大拇指,低声道:“明智!今日的戏目,把陛下的底线逼出来了。下面,可以捧杀那个阉人!”
杨寄苦笑道:“我没想那么多弯弯绕。朝堂里热死我了,哪有心思听他们玩权术,只想着早点离开才好!可惜在宫门口竟没来及问下太医,什么玩意儿能解鹿血酒的热性!”
沈岭挑了挑眉,瞥眼看看杨寄红扑扑的脸,差点笑出声来:“我倒是无心插柳,是不是救了你的大急?”
杨寄很认真地纠正他:“是救了你妹妹的大急。说真的,我就快打熬不住了!”
沈岭在马上给他作了个揖:“那么,我替阿圆谢谢你!阿末,你憋得辛苦了!”他忍不住想笑,但还是厚道地说:“到将军府找个空房间盘桓一下,晚些回去,然后可以借口说天快亮了,好好补一觉。”
刚刚有事情忙着能够分分心,现在闲下来,杨寄只觉得浑身不对劲,抓耳挠腮地难过,习惯性地到了将军府,他飞身下马,对司阍的第一句话:“哪间屋子空着?”
接着,就以三急之时奔厕所的劲头速度,到那间屋子里不知做什么了。
过了好一会儿,里头一层层传话出来,说将军要请沈主簿。沈岭进那间屋子时,杨寄满面通红,扶着柱子正在系汗巾。他苦笑着摇摇头:“自己不行,不解渴……”
沈岭低头默然了片刻,说:“阿盼想阿母,想得都病了。你火速送她去秣陵吧。”
杨寄也愣了片刻,旋即想明白了。宵禁算什么!城门算什么!三刻钟的马程算什么?!他兴奋得有些难以遏制,跳起来道:“好!快给我备马车!”
沈岭见他两只眼睛飕飕冒光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吩咐下去,又说:“给我也备一匹马——将军带小女郎先行,我在后头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