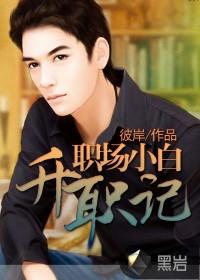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嫁给我吧杨贵妃 > 第95页(第1页)
第95页(第1页)
她正想着,突然感到车速慢了下来,开始以为是即将进城,让圣人车驾先行,可等了半天,车竟然停了下来,她心中疑惑,掀开车帘看去,却大吃一惊。马车不知何时已经偏离了官道,来到山脚下,前后哪里还有其他马车的影子,连车夫也不知去向。她心中一惊,不知发生何事,让孩子们在车中不要出来,自己慢慢下了车。脚刚落地,便被人从后面抱住,她以为遇到歹人,情急之下就要呼救,却听那人轻声在耳畔说:“是我。”她整个人僵在那里,一时恍惚了。这熟悉的声音在梦里出现无数回,以至于,她怀疑自己此刻是不是还在梦中未醒。就这么呆呆的站着,不敢回头,生怕看到的是一个幻影,梦就醒了。脸侧贴上了温热的脸颊,轻轻蹭着她,那触感如此真实,她禁不住伸出手去,轻轻摸着那张脸,迟疑的问:“十八郎,是你吗?我是不是在做梦?”一只大手紧紧握住她的手,用力得让她有些疼,也令她明白,自己绝不是在梦中,这才猛地转过身来,身后果然是那个朝思梦想的人,顿时眼泪流了下来:“真的是你,是你……”她哽咽着,泣不成声。李瑁微笑着看着她,却也眼中带泪,轻声说:“是我,都是真的,你终于回来了。”他说罢紧紧将她抱在怀中,喃喃说道:“整整一年五个月零六天,终于回来了,从今日起,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一生都不要跟你分开。”玉茗在他怀中,此刻才感受到回归的安宁,这一年半漂泊在外,如今,她终于又回到他身边。两人就这般抱着,沉浸在久别重逢的喜悦与激动中。直到两个孩子在车中等的着急,偷偷掀开车帘,看到许久未见的父亲,雀跃着跳下车来扑了过来,李瑁才轻轻松开她,笑着一边一个抱住两个儿子,笑道:“一家人,终于团圆了。”他让母子三人先上车,自己让护卫牵了马,自己则亲自驾了马车。马车慢慢启程,玉茗此刻仍有些恍惚,这一切仿佛梦一般,她却知道一切都是真的。她坐在他身旁,见他不时看着自己,脸一红,低头笑道:“十八郎为何这般看着我?”李瑁抿嘴一笑,握了她的手说:“以前便每日都看不够,如今隔了一年半未看,定要将你印到心里去才能缓那相思之苦。”他的话让她心里一暖,手被他握着,即便是在这初冬微冷之时,也感受不到一丁点寒意,反倒整个人都热乎起来,暖暖的十分舒服。她问起马车为何会来到山上,李瑁神秘一笑说:“我们并不回十六王宅,也不去长安。”她一听,以为新帝继位对他不利,脸色一变,刚要问,却被他轻轻摇头打消了疑虑,只是,他却不肯说究竟要去哪里,只说到了地方她就知道了。马车沿着蜿蜒山路慢慢前行,没走多久便停了下来。李瑁先跳下车,轻轻扶着她走下来,又抱了两个儿子下车。玉茗环顾四周,发现这里竟然是城外当年他们来过的别院。她吃惊的看着李瑁,问道:“为何带我来这里?”李瑁轻轻一指那门上牌匾,问道:“你可看到上面写了什么?”她顺着看去,只见上面写了三个大字:寿王府。心中一愣,莫非……只听他笑着说:“新帝登基后要讨伐叛军,让我带了其中一支唐军,并要封我为将,我却没有答应,只跟他说了一个要求,若是有一日能收复长安,请他允许我们破例不住在十六王宅中。”“我曾答应你带你离开那里,就一定要做到。本以为,两军对峙这么久,不知何时才能了了这心愿,没想打安禄山被儿子所杀,这便是天助我大唐。待两个月前唐军攻下长安城,又得知你们已经从蜀地启程,我便跟新帝求了这别院作为新王府。”玉茗听了,既是欣喜,有时担心,她问道:“新帝登基不久,连太上皇都被他缴了卫队,你这般做,会不会……”自古皇帝多疑心,特别是李瑁又是皇弟,就算李亨不多心,难免有人进谗言。李瑁却摇了摇头,笑道:“我一到长安便自动将兵权上交,只安心修葺这里,想着在你到来之前让这里焕然一新,给你个惊喜。好在这里僻静,没有被破坏太多,终于赶在几日前完工。”他拉着她和孩子们走进大门,果然府中布置与上次来时细致不少,甚至连花草也已种上。两个孩子来到新鲜地方,立刻就跑了过去,瞧这看那,十分新奇。玉茗见这里虽没有十六王宅气派,却清净自在,舒心得很,她长长的舒了口气,这一年多来郁结于心的不安、担忧和思念,在这一刻全部呼了出来,整个人神清气爽,连头顶的天都觉得分外蔚蓝。李瑁让护卫照看着两个孩子,自己则拉着玉茗走到后院,玉茗来到院中,一眼便看到花坛里的玉茗花,惊喜道:“这花竟然还活着?”说着便走了过去。李瑁跟在她身后,笑着说:“我本也以为叛军占据长安这一年多,恐怕将王府砸抢的不成样子,这花想必活不了了。没想到虽然府中财物被抢,屋舍被毁,可花坛中虽杂草丛生,却没有受到多少毁坏。”他叹了口气:“只是花堂中的几株玉茗花因无人照料,多半没有成活,只剩下这一株靠着雨水活下来,却奄奄一息。我便死马当作活马医,将它移了来,看看能不能成活,或许老天爷让它替了你陪我,竟然慢慢的发出新枝来。”玉茗看着那有些凋零的枝叶,虽大伤元气,却也慢慢地缓了过来,感慨道:“在这乱世中,连花都顽强的活着,生而为人,又怎么能轻易放弃?”她跟李瑁坐在新屋廊下,说起这一年多的经历,说到贵妃的死,不仅黯然神伤:“想来她也是命苦的女子,许多事都无法做主,还要被世人误会是妖媚误国的奸妃。”李瑁见她说着说着便难过起来,拍了拍她的手说:“一切自有天意,她虽不能做主,最后不得善终,可终归是当了十几年太上皇身边宠极一时的妃子。她最后不也说并不后悔吗?不管是否口是心非,她想必最后已经没有遗憾。”她点点头说:“我明白,想必她与太上皇之间是真的有情,只是,涉及家国,终归无法相守。”她突然想起一事,忙问道:“广平王可知珍珠在洛阳落难的消息?”李瑁点点头:“我也是听他说才知道此事。广平王也不知当初启程时并未带上她,以为有适儿在那,太子定不会舍弃孩子的生母,没想到张良娣暗中安排人将孩子抱走,又将沈氏锁在后院,留她独自在长安城中无依无靠。”玉茗一听,才知又是张良娣捣的鬼,她从来没有恨过一个人,即便张良娣多次针对她,也只是厌恶不想接近,可听说珍珠也是被此女所害,可见她是多么恶毒,不由咬牙切齿:“她未免太蛇蝎心肠,自己也是有儿子的人,怎么忍心看着别人母子分离?”李瑁知道她曾多次被张良娣设计,再加上沈氏的事,心中难免不忿,宽慰道:“事到如今,还是看看如何能救出沈氏。至于张良娣,虽说她如今已经封后,为后宫之首,可我们远离宫廷,她也无法奈我们何。”他想了想又说:“况且,她屡次三番针对广平王,想必也不会甘心让他将来继位,怕有要引来一场是非。”玉茗这一年多来虽过得并不舒心,可却少有这些勾心斗角之事烦心,可一回到长安,便又要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宫廷争斗,方才还轻松而心情顿时有些压抑。她将头轻轻靠在李瑁肩上,闭上双眼,感受他熟悉的气息传来,将那些不想面对的事情抛之脑后。耳边传来久违的大慈恩寺钟声,让她的心慢慢沉静下来。不管怎样,只要他在身边就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