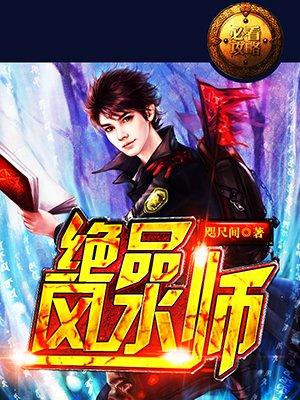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护士被砍死案件 > 第99章(第1页)
第99章(第1页)
他说:「那不可能。你的过去是证据的一部分。我不能在我的报告中扣下一些证据不报,或是省略相关的事实。我不会选择那样做。如果这样做了,我就应该放弃我的工作。不只是这件案子,还有我的职业,而且是永远。」
「你当然不能那样做。像你这样一个男人没有工作会是什么样呢?而且是这种特殊的工作。你会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容易受伤,甚至会不得不开始像个普通人那样生活和思考。」
「你无法用这个说动我。为什么一定要说这种羞辱你自己的话呢?我们有法规,有制度,还有誓言。没有这些,任何人都不能安全地做好警察工作。没有它们,埃塞尔&iddot;布鲁姆费特就不会安全,你也不会安全,伊尔姆盖德&iddot;格罗贝尔也不会安全。」
「这就是你不愿帮助我的原因?」
「不完全是,我不能选择那样做。」
她伤心地说:「不管怎样,你这话说得很诚实。你就没有过疑惑吗?」
「当然有。我并不是那么傲慢的人。疑惑是不会消失的。」他的确有疑惑,但那是理智上的、哲学上的疑惑,它们并不折磨人,并不会紧紧抓住你不放,曾使他彻夜沉思多年。
「但是有法规,不是吗?还有制度,甚至还有誓言。它们是最为便利的盾牌,如果疑惑变成了麻烦,就可以藏身其后。我知道,我自己也曾经藏身其后。你和我毕竟不是完全不同的人,亚当&iddot;达格利什。」
她拿起椅背上的斗篷,系在肩膀上,然后微笑着站在他面前。看到他虚弱的样子,她伸出双手抓住他的手,扶着他站起来。他们面对面站在那里。突然,前门的门铃响了,几乎同时,嗡嗡作响的电话铃声也响了起来。对于他们两人来说,这一天又开始了。
第九章夏天的尾声
1
9点刚过,电话便打过来了,达格利什走出伦敦警察厅,穿过维多利亚街,行走在清晨的一片雾霾之中,这雾的确兆示着今天又是一个炎热的八月天。他毫不困难地找到了那个地方。这是一幢高大的红砖建筑,位于维多利亚街和赫斯费利路之间,虽然不是特别破旧,但看起来使人很压抑、很沉闷。它是一幢实用的长方形大楼,正面凹陷进一列不成比例的窗户。没有电梯,他毫不犹豫地走上三段铺着亚麻油毡布的楼梯到达顶层。
楼梯平台处发出一股汗酸味。房间外面,一位身体臃肿的中年胖女人,系着一条花围裙,正在劝说一个值勤的警察。她的声音就像那种患腺体肿大的病人特有的哀鸣声。达格利什走近时,她转身向着他,滔滔不绝地夸张地发出一连串的抗议和声诉。哥尔德斯特恩先生要说什么?她真的不能分租出一间房子来。只有经过房东太太的同意她才能这样做。现在这间房,想都不要想。
他从她身旁走过,一声不吭地走进房间。这是一间正方形的屋子,里面非常闷热,散发出家具抛光油的气味,室内刻意的装饰还是十多年前流行的样式,满眼是当年厚重韵味的象征品。窗户开着,带花边的窗帘也拉开了,但是空气还是不流通。警务医官和随从警察,两人都是高个子,似乎已经把这里所有的东西都用过了。
又是一具尸体呈现在眼前,只是这一具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内了。他只需要看一看,彷佛在核实一个记忆。看着躺在床上那具已经僵硬的尸体,他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兴趣注意到那只左臂松松地悬在身体的一侧,长长的手指屈曲着,一个皮下注射器还插在衣袖内侧,就像一只金属制的昆虫用它的尖牙深深地刺进了柔软的肌肉中。死神一点不曾把她的个性消除掉,至少目前还没有。不久之后这具躯体也会腐烂,死神会在上面尽情侮辱,使它尊严丧尽。
警务医官未穿外衣,只穿了衬衫,满头大汗,不断地解释着,彷佛担心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他从床边转过身来,达格利什才明白他是在跟自己讲话:「因为苏格兰场离这里很近,第二封信又是写给你个人的……」他犹豫地停住了。
「她给自己注射了伊维派。第一封信上讲得很清楚。这是一件明明白白的自杀案。这就是为什么警察不想给你打电话。他认为不必麻烦你过来。这里真的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达格利什说:「我很高兴你还是打了电话。这算不上麻烦。」
有两个白色的信封,一个封了口,是写给他的,另一个没封口,上面写的是:「有关人员收。」他不知道她写下这句话时是否笑了。当着警务医官和警察的面,达格利什打开了信封,字写得坚定有力,墨迹很浓,笔画长而尖。他很吃惊地想到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她的笔迹。
他们不相信你,但你是对的,是我杀了埃塞尔&iddot;布鲁姆费特。这还是我第一次杀人;你应该知道这点,这很重要。我给她注射了伊维派,等一会儿我也要对自己这样做。她以为我给她注射的是镇静剂,可怜的、轻信的布鲁姆费特!如果我给她尼古丁,她也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它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我以为我能为自己开创一种有益的生活,但是不能,我的性情不容许我生活在失败之中。我不后悔我做过的事。这对医院、对她、对我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我是不会因为亚当&iddot;达格利什把他的工作看作道德法则的化身而被吓住的。
她错了,他心想。他们没有不相信他,他们只要求他找出证据来,这也是合情合理的。虽然他继续调查这个案子不松手,彷佛它是他个人的一件深仇大恨‐‐恨他自己,也恨她‐‐但他当时和后来还是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她什么都没有承认,而且任何时候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惊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