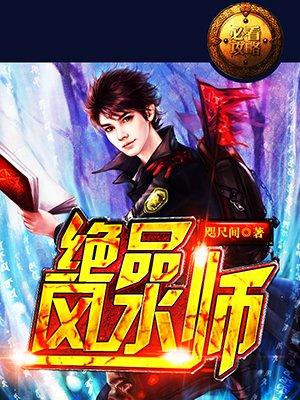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护士被杀害 > 第34章(第1页)
第34章(第1页)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牛奶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
她们俩几乎是齐声驳斥他,而且声音都很平静:「啊,没有!如果有,我们还会继续往里灌吗?怎么可能呢?」
「你们还记得启开瓶盖时,它像是被拧开过吗?」
两双蓝色的眼睛互相望了望,几乎像是在传递信号。然后莫琳回答:「我们不记得它是否被拧开过。但即使有,我们也不会怀疑有人在牛奶上动过手脚,只会认为那是牛奶房的人按习惯做的。」
雪莉说接着:「我认为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注意到牛奶有什么问题。要知道,我们当时正专注于滴灌的步骤,要保证我们需要的一切工具和装备到位。我们知道比勒小姐和总护士长随时会来。」
这就是解释。她们经过培训,是知道要注意观察的女孩,但她们的观察有其特定性和局限性。如果要她们观察一个病人,她们绝不会漏掉任何症状和征候,哪怕是眼皮的眨动或是脉搏的变化。然而对于房间里发生的任何事情,无论多么惹人注目,她们都可能注意不到。她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示范过程、仪器、装置和病人身上,会理所当然地认为那瓶牛奶没有问题。然而她们是农民的女儿,她们中的一员,莫琳,切切实实地将那东西从瓶子里倒了出来,难道她们就真的没有看出那不是牛奶的颜色、质地和气味吗?
莫琳好像看穿了他的心思,说:「这不是我们能否闻出苯酚气味的问题。当时整个示范室里都是这种气味,柯林斯小姐向来到处喷苯酚,彷佛我们全都是麻风病人。」
雪莉笑起来,说:「苯酚才不能治疗麻风病呢!」
她们互相望着,像共犯那样笑得很快乐。
谈话就这样进行着。她们没有提出可供思考的信息,也没有提出任何建议。她们不知道谁会希望佩尔斯或是法伦死,两次死亡事件发生之后,她们似乎也没有特别吃惊。她们还能回忆起凌晨与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讲过的每一句话,然而那次相遇明显没有给她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当达格利什问到护士长是否流露出了什么异常的忧虑或是沮丧时,她们同时盯着他,困惑地皱起眉头,然后回答说护士长表现得和平常没什么两样。
马斯特森彷佛在跟随他上级的思路,说道:「只差没有直接问她们,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看起来像不像是刚杀了法伦回来,你无法把话讲得更明白了。她们俩真是不爱说话的一对怪女孩。」
「至少她们确定了时间。7点刚过,她们取了牛奶,拿着它直接走进了示范室。她们为示范做初步准备时还没有打开牛奶瓶。她们大约8点40分回来继续完成准备工作时,牛奶瓶仍然在盘子上,仍然没有打开。她们把它竖着放进热水中,使其达到人体血液的温度,此后它一直在那里,直到她们将牛奶从瓶中倒入量杯内,大约两分钟后,比勒小姐和总护士长一行人到了。大多数有嫌疑的对象在8点到8点25分之间一起进早餐,因此下毒的时间要么在7点25分到8点之间,要么就是在早餐之后到双胞胎回到示范室之前的短短间隙内完成的。」
马斯特森说:「我仍然感到奇怪,她们居然没有注意到牛奶有什么异样。」
「也许她们注意到的东西比现在意识到的要多。但毕竟她们的故事已经讲了无数次,现在又重述了一遍。在佩尔斯死后的那几个星期内,她们最初的表述已经固定在头脑中,变得难以改变,覆盖了事实。这就是我没有问她们关于牛奶瓶的关键问题的原因。如果她们此时给了我错误的回答,以后她们就再也无法去更改它。我们必须给她们一次更大的震动,使她们完全进入回忆之中。她们现在没有用全新的目光去看发生的事。我讨厌重建犯罪现场,它们总使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虚构故事里的侦探。但是我认为可以在这里重建一次。明天一早我要去伦敦,你和格里森可以在现场监督,格里森大约会很乐意干。」
他简短地向马斯特森交待了自己的想法,最后说道:「你不必惊动护士长们。我希望你向柯林斯小姐要一些消毒剂。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一定要小心那些东西,事后把它处理掉,我们不能再让悲剧发生。」
马斯特森警官把杯子放进水槽,说道:「南丁格尔大楼真是厄运不断,但是既然我们在这儿,就不可能再次看到凶案重演。」
后来发生的事证明,这句话竟预言得一点也不正确,真是奇怪。
5
自那天上午早些时候在杂物间遇到达格利什以来,罗尔芙护士长有足够的时间从震惊中恢复,考虑一下她的处境。正如达格利什所料,她现在处于最不愿意配合的时候。关于示范课和胃内喂食的安排,以及佩尔斯护士死的那天早上自己的行踪,她都向贝利警察做过一番清楚、明确的交代。她对自己那番准确而一丝不乱的陈述做了确认,承认自己早已知道佩尔斯护士将扮演病人,并语中带刺地指出否认这一点毫无意义,因为法伦生病的时候,玛德琳&iddot;戈达尔来通知的正是她。
达格利什问:「你就没有怀疑过她生病一事的真假吗?」
「什么时候?」
「当时或现在。」
「我想你是在暗示法伦可能通过装病促使佩尔斯代替她,然后又在早饭前偷偷溜回南丁格尔大楼对滴管下手?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回来,但是你最好从脑中把她假装生病的念头去除掉。法伦根本不可能制造出398摄氏度的体温、寒战和飞快跳动的脉搏。她是那天晚上的重病号,后来几乎病了整整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