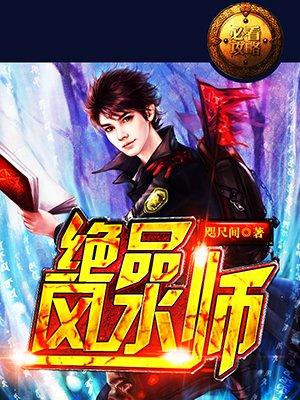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自作多情番外 > 第42页(第1页)
第42页(第1页)
宋峭从警察局做完笔录回来,夕阳的余晖透着玻璃窗照进来,有风从未合上的窗吹进来,沈云清蜷在被窝里,只有一撮黑毛露在外面。
他怔了怔,特意拜托过的护士打电话告诉自己沈云清已经醒了,回来时还特意绕了远路,只是要买一盅适合沈云清喝的粥。
七月流火,外头吹起了冷风,拎回来的粥已经有些凉了。
宋峭把东西放在柜子上,小心的拖开椅子,弯下腰准备把沈云清从被窝里拯救出来。
沈云清以前睡觉的时候就像个离不开人的小孩子,整夜都要像个四爪青蛙一样贴着宋峭不放。
现在这样孤零零地一个人蜷缩着,眉头深深皱起,反倒让宋峭心疼起来。
大约是沈云清的脸太热,宋峭一不小心接触到他的脸,他就立刻反应过来,一把捉住那只手,又被冰的浑身一颤,半睡半醒。
他的眼睛还没睁开,不耐烦地压着嗓子问:“是谁啊?”
宋峭想把手抽回来,想要叫他起来喝粥,又怕他醒了难受,只好笑着哄他说:“没什么?”
沈云清听出来是宋峭的声音,十分惊喜,却还是不睁开眼,两只手握的更加用力,迷迷糊糊地说:“是宋峭吗?又做梦了。”
他说的声音很小,可在这样寂静的夜里,明明白白地传到宋峭的耳朵里。
宋峭撑不住笑出来,“哦,你不要睁开眼,一睁开眼梦就醒了,我就不见了。”
沈云清摇了摇头,鼻尖都是红彤彤的,把握着的手捏的更紧,小声说:“我不会睁开眼的。”
宋峭让闭着眼的沈云清靠起来,顺便拆开一旁的粥,搅匀开来,一勺一勺地送到他的嘴里。
开始宋峭以为是他在开玩笑,可喝完粥沈云清还是那副半梦半醒的样子,他才察觉到一丝不对劲来。
果然,沈云清的额头热的吓人。
宋峭要去找医生,沈云清不让他走,委屈地说:“我都没睁开眼,你为什么要走?”
后来忙了一夜,医生检查了一番,幸好不是因为伤口感染而发烧,只是受伤抵抗力下降,着凉感冒发烧而已。
沈云清挂着吊水,宋峭摸了摸他的脸,有点后悔,“早知道就不逗你了,也能早点发现。”
沈云清因为刚才丢脸至极,又不肯放开宋峭的手,闭着眼不肯说话。
吊完水已是半夜,宋峭也累的在一旁打瞌睡。沈云清没敢睡,用手小心翼翼地碰了碰宋峭的脸,仿佛在感受宋峭是不是真的存在。
宋峭睁开眼,看着他的目光明亮。
沈云清缩回手,掀开被子别扭着说:“陪我一起睡。”
宋峭钻进被子,不敢离他太近,凑在他耳边说:“别担心,我又不会跑了。明天早晨醒过来,你一定第一眼就看到我。”
是啊,他的宋峭又不会跑了。
沈云清终于安心下来,陷入香甜的梦境。
番外二
过了几天,沈云清总算能坐起来,警察获得了医生的准许,来给沈云清录口供。
来了两个警察,一个问,一个负责记录,颠来倒去,还是那么几个问题。
其实沈云清根本不知道那天冲上来的是谁,警察也问不出什么所以然,倒是记录的那个警察瞥了几眼在一旁满脸淡漠的宋峭,有些不自在。
直到提起这次的犯罪嫌疑人宋槐,沈云清才反应过来。
那是宋峭的父亲。
大约是沈云清出院的时候,电视上才放出新闻,说是秦笑因为涉嫌教唆他人犯罪而被逮捕。
沈云清看的愣住了,宋峭捡起掉在地上的遥控器,笑了笑问:“这么惊讶?难不成还心疼吗?”
沈云清说不准宋峭是不是和自己开玩笑,即便是开玩笑也不敢忽视,抓住宋峭的手把他往下拉,揣到自己怀里,紧张地说:“你别吓我,我只喜欢你一个人,以前的我干的蠢事不要再提,你提——”
宋峭的脸贴着沈云清的胸口,两个人亲密相拥,“你要拿我怎么样?”
沈云清低下头也看不清他的神色,无奈地叹了口气,面无表情地讲出自己的威胁,“我舍不得拿你怎么样,以前干了那么多蠢事,想来想去也只能惩罚自己了。”他的胳膊还有些力气,宋峭被搂起来,两个人的脸贴在一起,“峭峭你说,要怎么罚我?”
宋峭一听“峭峭”两个字,浑身发麻,伸手便要推开他,沈云清搂得更紧,宋峭怕碰到他的伤口,不敢用力挣扎,只好用头撞他的鼻尖,笑着骂,“你今年可已经三十八岁了,拿自己威胁别人,还要不要点脸!”
可沈云清一贯拿不要脸当成常态,摸了摸被撞疼的鼻子,继续同宋峭撒娇,“峭峭说要怎么惩罚我好呢?帮峭峭洗头?帮峭峭洗澡?帮峭峭按摩?要么,帮峭峭解决欲望,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