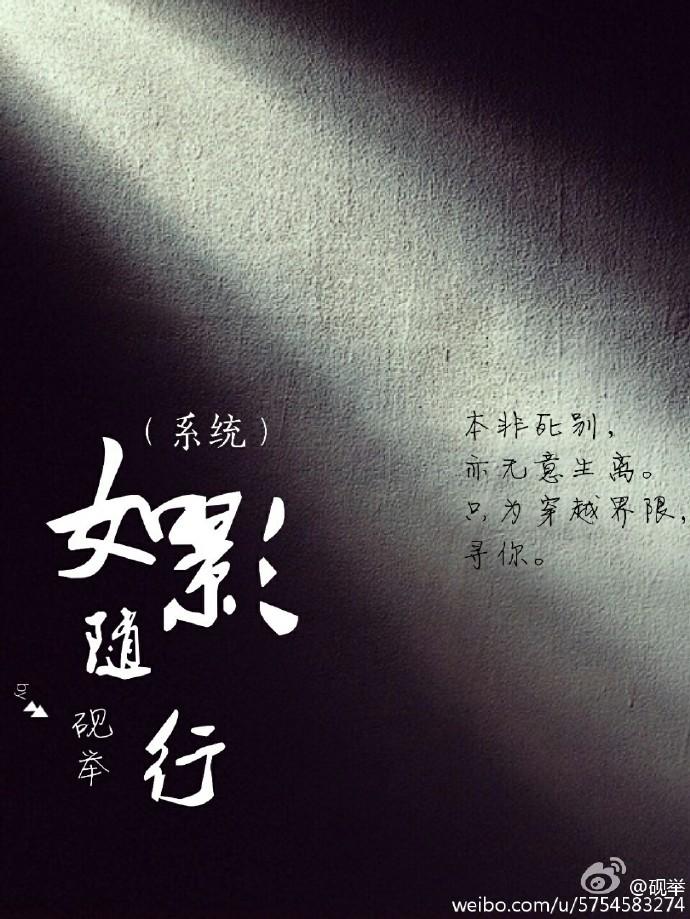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刘瑞明作品 > 爪哇国哈尔滨东京辨假(第2页)
爪哇国哈尔滨东京辨假(第2页)
回到“爪哇国”上来,它应是“早忘过”理据本字的隐实示虚,设难成趣。“早”与“爪”,“国”与“过”,在不同的方言中或近音,或同音(声调不论)。“挂”与“忘”的韵母差别较大,为了求趣,也就在所不计了。某种心情一下不由自主地顿失全无,也就是早已忘过了。由于“爪哇国”的虚假形式是名词,所以句中只好另有“钻过、落向、丢在、飞到、撇向”之类的动词作谓语。实际上这类动词是假上再作假,是令人不疑“爪哇国”属假的第二重机关,是这种说法的第二重巧智妙趣。
可以设想的一种情况:甲问:你方才的火气怒容哪儿去了?乙答:爪哇国(早忘过)去了。先有这样的说法,后有“钻过爪哇国”之类另带羡余动词的说法。在甘肃方言中,把失去机会,指耽误了的“耽过”一词,被谐音说成“耽果”,因而又有“吃耽果”的说法。又如“围上围脖”的说法中,都是同样的羡余现象。
也许“早忘过一爪哇国”的谐音解释不会被人接受,那我们再举几种方言中类似的一些词语来作对比证明。
例一,上海话“触霉头”与普通话“倒霉”同义,都是见字明义的。但上海话又有个趣怪的同义词,叫“触头哈尔滨”,见《方言》1985年第3期,许宝华等《上海方言的熟语(二)》,但该文也避言为什么会说到“哈尔滨”。此议它便是“瞎尔碰”的隐实示虚。上海话“哈”与“瞎”音值相近,差别只是“瞎”字带喉音韵尾。“滨”与“碰”读音相近。“触头、瞎尔
碰”是实际理据用字,是同义联合结构,趣意谐音说成“触头哈尔滨”,便成为在哈尔滨碰头的虚假意思,词的内部结构也另变成“动词、宾语、地点补语”了。
例二,马思周等《东北方言词典》:“热闹东京:形容很热闹的样子。隔壁唱大戏,热闹东京的哩。”词典也避言为什么牵扯上“东京”地名。这个“东京”不是从宋代洛阳作趣,而是从日本的国都作趣,又显然不是作比喻,因它并非是最热闹的地方。而且语言中也没有用某个热闹的外国大城市来比喻热闹的一般说法,只有“热闹得像某个处所”这种措句表述。东北方言此词中的“东京”只能是“动静”的谐音趣难说法。犹言热闹情况,即一片热闹。
例三,同词典,“云南戛戛国:犹九霄云外,极远世界。这件事我真忘到云南戛戛国去了。”词典也避作理据解释。
今议,云南对内地或我国北方地区来说,也确实远,犹如爪哇国之远一样,但同远或更远之地又很多,况且并无什么“戛戛国”,可见并不是以地方远的事理作比喻,当从字音谐音求趣。同词典:“晕:胡乱走。”“晕得乎:迷糊糊或飘飘然。晕头儿:发昏,迷惑。”晕、迷、忘,三者可同指,所以就把“晕”隐实示虚,说成“云”。两个字仅声调不同。晕与乱相关,而把“乱”谐音成音近的“南”字。而“戛戛”则是“旮旮(旯旯广的省写记音字),指某个角落。“国”是“过”的谐音作假,该词典中此两字仅是声调不同。词的本来理据只是“晕而乱的过到某个旮旮”的一句话,节缩、倒序、谐音而成为“云南戛戛国”趣难词。理据与用字风马牛不相及却相及了,可见群众刻意求趣,而综合使用各种语文手段。
例四,同词典“八:1虚指最多、最大。2转用义为‘乌有’、‘没影儿’。你这话说到哪八国去了!没那八宗事。”
按,“八”表泛说的多数,如“八百辈子”、“八瓣儿:形容非常破碎”,“八竿子打不着”等词中。其他方言和普通话中也如此。但由此必定不会反而引申为“乌有”、“没影儿”词义。正是词典对“哪八国”词中的虚假的“八国”不知奥妙而误说。“哪八国”当是“哪傍个”的谐音虚假趣说。“你说到哪傍个去了?”即说到不存在、不正确的某一方面去了。“没那八宗事儿”是一个节缩的说法:不仅没有这一宗事儿,也没有同类的八宗事儿。“八”仍虚指多数。所谓“哪八国”也是个虚假的国家处所名词,与“爪哇国”中类似。
例五,陈刚《北京方言词典》:“哈什罕儿:〈陈>喀什干。往往用来代表遥远的地方。|你是上云南、哈什罕儿去了?怎么去了这么老半天?”
按,“哈什罕儿”字面不成义,也不是哪里的实有地名,在例句中仿佛是个地名,而且是译音地名。它显然是有意而拟的假谐音地名,即在新疆“嘻什”城名之后再缀个“罕儿”的尾巴,造成一个假象,似乎是新疆的一个偏僻的地方,这便是一层趣意。以前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为了诽镑闻一多、吴晗拥护中国**,造谣说他们暗中接受苏联**的卢布津贴,并把二人的名字妄说成“闻一多夫”、“吴晗诺夫”,好像俄罗斯人名。其语文手段相近似。
嘻什自然距北京远,但比它更远之地多有,而且“哈什罕儿”又是乌有、子虚之地。所以,“哈什罕儿”的理据也不应是从遥远而言的。
“哈什罕儿”中的“罕儿”相当于“嘻什干”中的“干”。我们把它还原为“哈什干”来分析论证,可知它是“哙事干”即做哙事的谐音趣说。研究北京方言历史的学者已论证:东北方言的不少词语被吸收、融化到北京方言中。上述《东北方言词典》哈ha的第二义是“什么”。例句是:“谁也不知道黄榜上写的是哈。”“抽你们去帮检修班干活,为哈不去?”
例句中“上云南、哈什罕儿去了”连言,这证明了它实是前已申述的东北方言词“云南戛戛国”的曲折变化。原词义是趣说遥远的地方,这保留在北京此方言词的“云南”中,只是已被割裂而独立。原词中的“戛戛国”,“戛戛”见字不明义,“国”字更碍事理,于是被北京人改变成“哈什干”。如此,“云南哈什干”即“(上)云南哙事干”的实际理据。但后来的人渐次不知“哈什干(哙事干)的表里曲折关系,便误以为“哈什干”与“云南”同指复说,“哈什干”也是指遥远之地了。而它的老祖宗“云南戛戛国”本来正是如此。
长时不见某人之后的作问:到哙远地方做哙事去了?问地与问事是必然相关的。可以推想,由“云南戛戛国”词先舍去碍意的“国”字,由“戛”之音而变为“干”,填补问事的空白,成为“哈事干”。再隐趣为“哈什干”,因新疆伊犁河的上源叫“哈什河”。又再变成附会城市名的“嘻什干”,再与前有的“哈什干”讹混成“哈什罕儿”。
例六,《武汉方言词典》:“俄国二:旧时比喻极远处:把他丢(忘)得(到)俄国二去了。”连“俄国二”是什么意思,都因不知而避难不解释,怎么知道是用它来比喻呢?而且词义解释并不准确。把一件事忘得死死的,并不说成:忘到遥远的地方了。词义应就是:忘记了。应当是“屙过儿”的谐音趣说。“屙”与“俄”都音,同音同调。“国”与“过”谐音。“二”与“儿”谐音。“屙”,在武汉话也说“巵”,而谐音“罢”。“巵”,也就是“屎”,谐音同音异调的“事”。“罢过儿”或“事过儿”,都是结束,完毕的意思。某件事情已经结束,不再理会,也可以说丢过了。笔者曾就我的这个解释向《武汉方言词典》编纂者朱建颂教授请求指正。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也没有指出是哪个环节错误。承蒙赐答复:“前几年曾有人在本地报纸上写文章说:汉口有个俄租界,序列为二,故称俄国为‘俄国二’。此说不大可信,可做参考。”
但是,在武汉或汉口固可以把俄国说成“俄国二”,却没有什么道理能用“俄国二”指极远处。
以上“爪哇国”等词已是“无独有七”了。共同之处都是说到什么国,什么地方(真的或假的),实际上这些地方与词的理据都不相关,而是求趣难的虚假谐音用字。“爪哇国”云云只见于文人的小说,不是方言词,从上述后五例来看,它只应是个别文人仿方言词而创,被《水浒传》的作者采用,又为以后的小说沿用。这些情况充分说明,隐实示虚,设难成趣所造成的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作家也欣赏,这是汉字文化的一个方面。
(原载《汉字文化》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