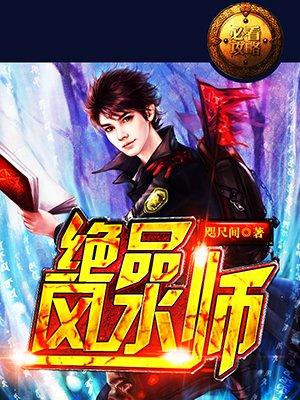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两两相忘是什么意思 > 第四十四章 配不上你(第2页)
第四十四章 配不上你(第2页)
吴若初毫无防备地吸了一口气,所有幻梦顷刻间被击碎,她脱离他的怀抱,觉得自己的声音像从遥远的地方飘来,“为什么?”
“我配不上你。”
“你还拿这种话来搪塞我?我说过!我不要你的钱,也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既然你也喜欢我,我们有什么不可以?我要你告诉我,到底为什么!”
她紧咬着方才被他吻过的唇,忍了忍,还是止不住落泪,泪痕连成闪烁的长线,先前绯红的脸色透出了憔悴的青白,她受够了他的反复无常,今天,她无论如何也要得出一个能让她信服的答案。
她哭得微微抽气,看上去那样楚楚动人,而又那样倔。他从未见过她哭,她一直是无忧无虑的乐天派,就算天塌下来也深信头上漂亮的阳伞可以挡住一切危难,可就是这样的她,竟然也会有这般仿似心碎的眼泪。
“魏荣光,你这个骗子。”她抽噎之中只得这一句。
魏荣光将她重新抱紧,拍着她的背,像哄一个孩子,她的眼泪掉进他脖子里,起先是热的,后来慢慢变得苍凉。过了许久,她哭累了,只剩下间或一颤一颤的吸气,埋在他胸口,近乎是说着胡话一般,“告诉我……告诉我为什么……别再这样折磨我……”
半晌,她听到头顶传来他的声音,咬字像是下了极大的决心,“若初,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他拉着吴若初坐在了沙发上,将她的手包覆于掌心,又逐渐变为十指相扣。吴若初心里有强烈的紧张,全身都出着冷汗,却没有一丝惧怕,她就是要知道真相,无论这真相是什么样的,都不可能动摇她对他的爱。
“从前……一般故事都是这么开头的吧……”魏荣光攥着她的手又紧了些,“从前,有个孩子……他很普通地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时候,别人还不叫他杀人犯的儿子……别人都说,他是来历不明的野种,说他妈妈不知道和什么男人搞在了一起,才生下了他。”
二十年前,魏荣光的外公外婆看见女儿跪在面前说怀孕了,惊得无法言语。
女儿魏念萍是个本分的姑娘,平日里贤良温秀,孝顺知理,从不需要父母操心,谁又能想到她会干出未婚先孕的事?父母追问她,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你是不是被什么王八蛋给骗了,可她缝紧了牙关,一个字也不说。
魏念萍的父母想破了脑袋也猜不出女儿会和什么男人有一段情,她身边好像从来没有亲密的异性,就连她最好的朋友小陶也说,虽然魏念萍曾经支支吾吾地提起过喜欢上了一个人,却没有讲出那个人的名字以及任何信息。
魏念萍的父母全力主张将孩子拿掉,女儿还这么年轻,这种没脸面的事情要是传出去,以后还怎么做人?不仅是她,就连孩子的脊梁骨也要被人戳断。旧城区的居民普遍思想保守,个个都可以变身卫道士,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只会指责魏念萍行为不端,却不会对这个无辜的孩子抱有过多的仁爱。
魏念萍面对父母的力劝,仍是一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样子,说什么也要把孩子生下来。
后来魏婆告诉魏荣光,“当年我对你妈妈撂过狠话,我说,要是她不去堕胎,我就不认她这个女儿……世上的事儿真是讽刺,我那时候一心不想要你这个外孙,谁知道临到头来,我也就剩了你一人。”
哭也哭了,恨也恨了,最后魏念萍生下了孩子,魏公魏婆又怎能不要这孤苦无依的一对母子。
魏荣光一天天长大,他对这个世界比较基础的认识之一就是,自己没有爸爸,而周围的许多孩子都因此而嘲笑他。关于这一点,他虽然苦恼过,却还是能够平心接受,妈妈很爱他,外公外婆也很疼他,这就够了,他有一个很好的家,即使这家中缺了某个令他日思夜想的成员,那又有什么关系?
一家四口的日子过得比较拮据,虽然魏公经营着一间汽修厂,但那个年头,路上的汽车并不多,厂址所在的地段也尚未进行商业开拓,汽修厂生意即使谈不上惨淡,也只是勉强可以维持的程度,魏公时常勒紧裤腰带,却没有一次拖欠过厂里员工的薪水。
魏念萍在一家小服装店工作,下班后还会接一些给人洗衣的活儿,她宁愿自己累一点,也要多挣点钱,让儿子过得舒坦些。大冬天里,她的双手长时间泡在冷水里洗衣,原本纤长白净的手渐渐冻得红肿开裂,经年难愈,手臂也有了关节炎,变天时疼得直咬牙,每当这时,魏荣光就会笨笨地踩上凳子,从柜顶取下伤药,用小小的手替她轻抹。
魏荣光刚记事的那个春天,他被母亲带到院子荒芜的一角,母亲手里拎着水桶和树苗,他拿着小铲子,母子二人合力将稚弱的小树苗栽进了泥土里,风过时,树苗悠悠招摇,像是在向他们母子致意。
母亲柔淡的微笑印在他懵懂的眼睛里,“这是海棠树,它会和小荣一起慢慢长大,小荣开心的时候,它也会开心,它就是小荣的好朋友。”
年幼的魏荣光望着小树苗许久,“它也没有爸爸吗?”
那时他相信,自己也是从泥土和尘埃里而来,是妈妈亲手栽出了他,只要妈妈在身边,春夏秋冬,他没有什么好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