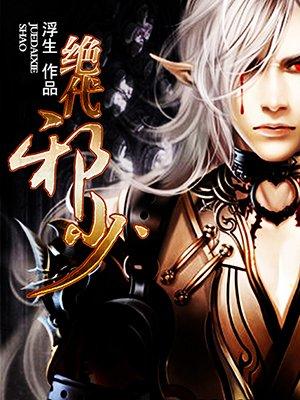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收秋和秋收的不同 > 第10页(第1页)
第10页(第1页)
“话说最近你突然对植物那么感兴趣?”我拍了拍他的背,他一激灵地站起来。
“你可吓死我了。。。。。。我不过是突然想看罢了。。。。。。”
但不过半晌,他又开口了,“你见过我们桌子上的花瓶吧?”
“还真没太注意,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东西。。。。。。”
“你不觉得。。。。。。”刘朝咬了咬嘴唇,逡巡了一阵,又最终缓缓道,“它挺像那朵花的嘛。。。。。。”
我忽然间想到了那一天的情景。曾经有一朵紫色的花,随着时光列车驶向远方。如今不知花身在何处,原来他果然还是挂念着它的呀。
“你是说火车上的那朵紫色的花吗?”我宽慰道,“这几天不记得了,真是对不起。我是真的没注意那花瓶里究竟放的是什么花。不过。。。。。。”我拿起旁边的几块早上买来的潘饼,“我当时看到这花,我就想起好像在《雾府新志》里有类似的描述。”
我拿出手机开始翻阅,“欸,你看着张图片,这个景点据说就存在大量这样的花呢。”
刘朝一下子凑过来,“真的有这样的地方吗?”
“好像是在五号线的终点站那边,一个瀑布下面有天然形成的这种花的花海。唉,我知道你肯定又想去了,这次能不能等我先把这潘饼给吃完?”
“先等等,我先确认一下。。。。。。那个景点是叫什么?”
“叫做飞梓朝花呢。”我抬眸望向刘朝不可置信的神情,“那种花,和你的名字。。。。。。”
“是有关系的吧?”
26
“我家乡有一种花叫做朝花,那种花开在百花凋零的九月。据说我爸爸和妈妈就是在这紫色的朝花海中结婚的,于是我生下来就取名叫刘朝。我这次远足,刚好碰上了花期,于是妈妈寄过来一朵朝花,以寄情思。是我不好,没有保管好它。。。。。。”
“那花是你的象征,你还在这里,何必在意呢。你再说往前看呀——”
离海滩五六里的悬崖上,急湍由崖上飞驰而下,奔入大海。而这一水两翼,全是开得正艳的朝花。这紫色的地毯尽头便是梢梓里的村庄,夕阳正从那边的屋檐缝隙间透过来,碾碎了,平铺在这花上闪闪发亮。
刘朝在原地久久没有反应。我把他僵直的身子移到旁边的一张长凳上,虽然看起来这凳子是历经世故,但居然也并不脏。
他坐下来后,转过头去,凝视着旁边的一朵花。这花应算是灌木,花刚好就在他眼界的平行的位置。
就这样看着。
我们坐车到“梓园”站下车,这个梓园虽是有个固定的大门,但并没有篱笆与围墙,这和我在越市游览到的海滨公园也不太一样。那个孤零零的大门上有一位不太知名的艺术家留下的“梓园”二字,看起来也已经被历史尘封许久了。他留下的署名叫华武先生。旁边两棵梓树很高很高,门上还垂下了几条蒴果悬挂,路上碎叶满地,与旁边的朝花相映衬,很是不同。
这片地区唯二的两棵梓树就伫立在这里,将这片梓园的这个迷你的大门荫蔽。
所以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呢。
好花时节不闲身。我坐在花海旁的一块大石头上,拿笔簌簌记录下一些文字,又拿起手机,迎着阳光拍了几张朝花的照片。
这次刘朝的花留下来了。
27
下雨了。
上周本来还晴空万里的天气,忽然转阴,淅淅沥沥的小雨就来了。这雨倒也不像是大雨一样酣畅淋漓,却只是一点一点下着,早晨大雾弥漫,我甚至都看不清桥下五十米外的站口。
这雨落在泥地上花叶生发,落到房屋上浮光片瓦,愈愿看透,愈变得朦胧。
其实我也不是没有赞美过这样的雨。在大学期间的征稿中,偶尔越市也在下雨,这雨便是我曾求索的方向。我曾多么希望某一天能站在越市某个公园未央,用手拥抱这雨。而我现在在清丰站台下,却并没有任何遐思。
我走进这雨,这清丰站旁就是浦下街。那是一个古代曾存在的郊野景致,而现在上面覆盖着是青砖瓦房。但在迷雾之中,周围的一切其实都不重要了。不论是有人有房有物,都凝结成一个小点和几抹淡色,穿梭于其中倒本来就该是十分享受的过程。可是我现在却不这么想。
因为心境变了。
我来这里快一个月,新鲜感很快就会过去。我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不知道我是否喜欢现在的生活。因为无知,所以恐惧,所以迷茫,所以才会在这样的雨天在这里,手拿着伞,却没有打开。有首歌说越长大就越孤单,越长大就越不安。现在回首望之,周围的朋友越来越少,曾经的人早就断了关系,未来的人还在雾中,我够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