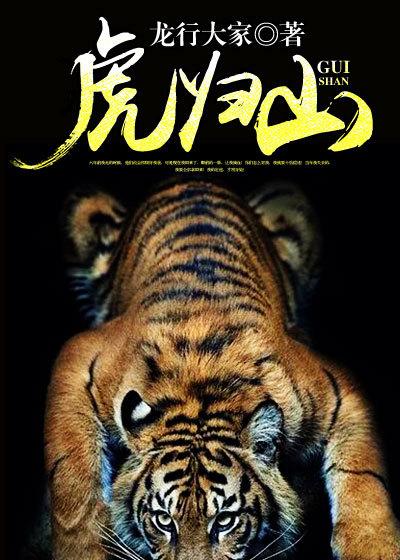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无污染无公害讲了什么 > 第15页(第1页)
第15页(第1页)
孟天意看了她一眼,觉得这倒也是。俩人摸不着头脑地琢磨了一会,没什么头绪,只好各自支摊干活。就在这时,几个民警步履匆匆地走过来,逢人就举着张照片问话,后面还跟着喻兰川。孟天意一抬头:“哎,小喻爷,于警官?”于严把帽子摘下来,抹去一脑门的汗,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孟老板,您在这太好了。”“又出什么事了?”“别提,还是上次那倒霉孩子。”于严说着,掏出刘仲齐的照片,“就这小子,昨天跟家里闹脾气,离家出走了,手机定位是在这附近,您见过他吗?”孟天意凑过去,仔细看了一眼,摇摇头:“没有,眼生,等我给你问问——杆儿!”甘卿正在往眼睛里塞隐形眼镜,不小心掉了根睫毛在里头,异物感一下把眼泪刺激出来了,听见孟老板喊她,泪眼朦胧地探出头:“嗯?”她还没来得及化那个非主流的妆,嘴唇颜色极淡,脸极白,一点血色都凝在眼周,在素白的底色上非常显眼,让人想起雪地里意外绽开的花。不知道为什么,喻兰川的目光和她碰了一下,下意识地移开了视线。“麻烦您看一眼这孩子,”于严连忙把照片递过去,“有印象吗?”甘卿看了好半天:“这不是那个……”于严:“对对,就是上次在这被人碰瓷的那个,您还帮忙报警来着,叫刘仲齐!附近见过他吗?”甘卿摇头。于严重重地叹了口气。就在他转身要找下一个人问的时候,甘卿忽然迟疑着叫住他:“您刚才说他叫什么?”“刘仲齐,伯仲叔季的‘仲’,齐是……”甘卿掏出手机,翻出她新加的那个“是仲不是齐”:“是这俩字吗?”泥塘后巷没有监控,只能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判断,刘仲齐小朋友在头天晚上十点半左右,来过这里,店门口有几个不祥的痕迹、一颗扣子——喻兰川这个不知道有什么用的哥,看了五分钟,也不能确定这颗扣子是不是他弟弟的。如果说,就这些这还无法断定小孩不是自愿走的,那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在垃圾桶里找到的手机,就很能说明问题了。手机被人暴力砸在地上,屏幕裂成了渣,机身已经摔散了。警报升级,青少年赌气离家出走事件,变成了绑架案。于是大家店也不用开了,菜也不用做了,星之梦门口那一块地方被圈了起来,一大帮警方的人忙进忙出。甘卿把聊天记录交给了警察,还被问了话,问完,这里也没她什么事了,于是她跟孟老板告了别,准备回家,走到小路口,却看见喻兰川正在打电话。喻兰川留给她的第一印象,就是那天那个敞胸露怀的德行,眼皮一耷拉,拽得二五八万一样,好像身后跟着一排照相机,等着抓拍他搔首弄姿的硬照。是个光鲜的少爷。但“少爷”对着电话,却又客气又有涵养,和周围的忙乱形成鲜明对比,甘卿听见他说:“……实在不好意思,我现在家里真的是有点事,走不开……”他话没说完,就被电话那边的人打断,甘卿隔着几步远,看见喻兰川暴躁地把眼镜摘下来,扔在警车车顶上,反复揉捏着鼻梁,表情就像想砍人,说话却依然是礼貌而且心平气和的,好像嘴脱离了身体,出来单干了:“我明白……是,理解,您看这样好不好,等我回公司,保证第一时间……”电话那头就“嘤嘤嘤”地开始吠,没完没了的。喻兰川就沉默下来,面无表情地抬起头,眯着眼看了看灼眼的晴天。及至一字不漏地把对方的话听完,他才深吸了一口气:“……那好吧,我联系我部门的人处理,您稍等。”接着,他就开始打电话,遥控部门,指挥下属们干活,让这个修改材料,让那个替他去开会,甘卿看见他靠在警车上,半闭着眼,条分缕析地跟同事们叮嘱会议要点,手指一直在揉捏着眼镜腿。长篇大论地说完,喻兰川口干舌燥,又回忆了一下,确认自己没有遗漏,这才对同事说:“行,就这事,辛苦了,你去吧。”同事礼节性地问:“喻总,家里怎么了?没事吧?”喻兰川:“我……”我弟弟失踪了,疑似被人绑架。“啪”一声脆响,喻兰川没控制住手劲,掰断了眼镜腿。“……事不大,”于是,他又把那句话咽了回去,“处理完我就回公司,随时保持联系。”没什么好说的,别说是丢了个中二弟弟,就是亲妈死了,又能怎么样呢?同事也就不痛不痒地说句“节哀”,嘴甜的,最多再客气一句“有事您说话”。心里一准就得犯嘀咕——他家怎么越忙越有事?上司死了妈,我们是不是还得表示一下?唉,红白事总在月底,不穷不来事。整个世界都在高速旋转,每个人都得疲于奔命。别人的天灾人祸、生老病死,那都是添乱的不速之客。喻兰川放下电话,发现了几步之外的甘卿,就冲她一点头:“麻烦了。”甘卿不知怎么的,一时冲动,脱口说:“你可以找杨大爷帮忙。”喻兰川惊讶地看着她。经她一提醒,喻兰川才想起来。据说在解放前,棍不离手的杨大爷曾是丐帮帮主,后来社会变了,不兴那些帮帮派派了,大家伙也都该找工作找工作、该退隐退隐了。现在丐帮里的老人们,一般只在衣服上留几个补丁,算是保持传统,平时都过普通日子,偶尔开展“文明行乞,抵制早晚高峰地铁要饭”的宣传教育活动,或是在乞丐们划分地盘起冲突时过问调停一下。但有这张无孔不入的关系网,他们的消息都是很灵通的。问题是,她怎么知道的?甘卿话一出口,就后悔得差点咬了自己的舌头,飞快地笑了一下,她脚下抹油,溜了。钻进泥塘的小杂巷里,甘卿的脚步忽然一顿,想起了那天在这一片跟踪她的光头——不怪她没有第一时间想起来,实在是这事已经过去快一个月了,当时正忙着讨生活,满脑子房租,这些鸡毛蒜皮没放在心上。她从包里翻出两半的木牌,心想:不会真冲我来的吧?被她念叨的光头正抱着宿醉的大脑袋,蹲在墙角,像一朵泡发了的大蘑菇。他的同伙刀疤脸在旁边驴拉磨似的乱转,转一圈叹一口气。这时,瘸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跑了进来,气还没喘匀,先看见了墙角被捆成一团的刘仲齐,差点把另一只脚也崴了。瘸子七窍生烟,大步颠到光头面前,抬起巴掌,劈头盖脸一顿抡:“你是不是疯了!昨天是不是喝假酒去了!是不是把脑浆也一泡尿呲出去了!”光头抱头鼠窜:“二师兄,哎,师兄别打,我错了……”“师娘那么大岁数了,整天在医院伺候大师兄,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你他妈没用就算了,还出去喝酒闹事,我打死你个闯祸精!”他们一行人被清理出租屋之后,就来到了一个城中村落脚。这个城中村早就说要拆迁,有几个钉子户坐地起价,补偿一直没谈拢,还不死不活地放着。其他拿了补偿的住户们已经搬得差不多了,见这地方一时半会也拆不了,就偷偷收钱,把破平房租给外地人。光头有酒瘾,那回去堵甘卿就是喝了酒,前一阵子被师哥和师娘看着,还算收敛,昨天晚上,那两位都不在,他一时心里痒,没管住自己,出门喝了个酩酊大醉,越想越觉得上次在泥塘后巷窝囊。酒壮怂人胆,光头把老太太嘱咐他的话丢到了十万八千里,醉醺醺地上门踢馆,结果扑了个空——人家店里早关门了。光头憋屈得“嗷”一嗓子劈了店门口挂的歇业木牌,正打算砸玻璃的时候,就听见旁边有人说:“你要干什么,我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