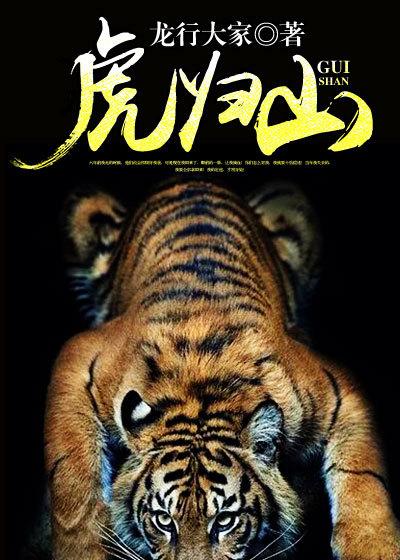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无污染无公害讲了什么 > 第8页(第1页)
第8页(第1页)
“哦,”孟老板尴尬地看了看她,又看了看警察,“我……这……下午客人太多,没注意外面。”“那几个人不是作为一个女青年,甘卿碰见当街敞怀的男青年,不能免俗地要多瞟一眼。瞟完,她觉得这具肉体要胸有胸、要腰有腰,拿出来展览一下也不算过分。就是……在这么一个地沟油和炉灰满天飞的小破地方,有必要时髦得这么努力吗?“我小时候在绒线胡同见过您一次。”喻兰川低头,目光扫过孟老板的手——孟老板的手很厚实,因为常年掌勺,沾着一点油渍,可皮肉却异常细腻,润得像玉,实在不像一双中年男人的手——对上孟老板迷茫的眼神,喻兰川隐晦地自我介绍说,“我姓喻。”孟天意和甘卿的脸上同时空白了一瞬。“哦,您!”孟天意把一直微微弯着的腰绷了起来,随后又压低了声音,“您……店里坐吧,请进。”说完,他朝一边摆摆手,刻意没往甘卿身上看,装出一副很随便的样子打发她走:“杆儿,没你事了,先回去吧,路上小心点。”甘卿在喻兰川出声的瞬间,就往后退了半步,从灯光里退了出去,本来就很低的存在感压得几乎没有了。听见孟老板发话,她幽灵似的点了下头,没吭声,转身就走。喻兰川本来没把她放在心上,习惯性地用余光一扫,正好扫见个模糊的侧影,他心里倏地一跳,脱口叫住了她:“等等。”甘卿好像被他吓了一跳,僵硬地站住,小心翼翼地回头问:“叫我吗?”她睁大的眼睛里满是惊惶不安,肩膀绷得很紧,战战兢兢的,像个受惊的野兔。喻兰川这时看清了她的样子,顿时一阵失望,心里翻腾起来的记忆忽地蒸发了。“没什么,”他神色淡了下来,疏离客气地说,“今天被他们拦下的是我弟弟,我跟您道个谢。”甘卿木讷地应声:“不、不客气。”喻兰川从鼻子里喷出口气,心想:“哪来的柴禾妞?话都说不利索。”他那点耐性还得留着伺候甲方爸爸们,很不耐烦这种“三脚踹不出一个屁”来的货色,克制地一点头,他就不再理会这个路人甲,抬腿进了“天意小龙虾”店里。甘卿想:“一惊一乍的,喻家准是祖坟让人扒了,出了个神经病。”她低着头,步履匆匆地走了,像一团不起眼的影子。泥塘后巷里的小路像迷宫,这个时间,除了露天烧烤一条街,其他地方都已经沉寂了下来,连夜风刮过,都凝滞了几分,年久失修的路灯亮不亮全看心情,有的还一闪一闪的。人在里面走,脚步声稍重就会起回音。怪瘆人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独自走夜路害怕,甘卿的拖鞋刻意在地上摩擦,还哼起了歌。她走到最背光的地方时,一个人影从她经过的小路口冒出来——如果刘仲齐在,就会认出来,这人是敲诈他的三个男人中的一个,那个光头的。光头恶狠狠地对着甘卿的背影盯了片刻,抬脚追了上去。他是个彪形大汉,身高足有近一米九,走起路来,脚下却没有一点声音。甘卿毫无察觉,顺着小巷拐了弯,静静的小路上,只有塑料拖鞋拖沓的脚步声,以及有些沙哑的女声:“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光头略微缩紧下巴,脚步越来越快,攥起拳头,手臂上暴起了狰狞的肌肉和青筋。“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光头猛地冲过了路口,然而随即,他脚下又来了个急刹车——眼前是个死胡同,漆黑一片,除了一辆报废的共享单车,什么都没有。人呢?这时,那“踢踢踏踏”的拖鞋声再一次响起,声音是从他后面传来的!“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光头猝然回头,看见那个多管闲事的“收银员”从他身后的路口溜达了过去,她插着兜,脚也懒得抬,走得东倒西歪的,一眼也没往他这边看。反正这附近也没人,光头干脆不再遮遮掩掩,吼了一声:“你站住!”吼完,他迈开长腿,去追甘卿。光头奔到路口,多说也就是五六步,一晃身就过去了,可是就这么眨眼的功夫,方才的女人再一次凭空消失了。“就把自己先搞丢——”那歌声的调子将跑未跑,回荡在小巷里,响得四面八方都是,光头的后脊梁骨蹿起一层冷汗:“你是哪一路混的,别装神弄鬼!”他这一嗓子吼出来,歌声和脚步声同时消失,一时间,四周只剩下夜风的低吟,窸窸窣窣、鬼鬼祟祟的。光头的心跳快起来,下意识地屈膝提肘,两手护住头,屏住呼吸,戒备地四下观望。突然,一种难以形容的战栗感流过了他全身,紧接着,一道不自然的风直逼他太阳穴,光头悚然发现,自己无论是躲是挡都来不及,他太阳穴上一阵刺痛,脑子里“嗡”一声,心想:“完了。”可是预想中脑壳被打穿的血腥场面并没有发生,光头愣了好一会,才发现自己连油皮都没破,他茫然地伸手摸了一把,大好的头颅安稳的待在脖子上。刚才仿佛只是风卷起了小沙石,正好崩到了他脸上。光头没头苍蝇似的在小巷里找了一阵,连个脚印也没捡着,正在运气,这时,兜里的电话响了,他摸出来一看,声气凭空低了八度,几乎说得上温柔了:“喂,师娘……我啊?我在下午那个小杂巷里,刚才正好看见警察在……您说什么?”他接完这通电话,顾不上再去找甘卿的麻烦,匆匆忙忙地跑了。离开泥塘后巷,又过了两个十字路口,跑出了一脑门汗的光头闯进了一家麦当劳。正在收拾桌子的店员被这凶神恶煞的大汉吓了一跳,猛地往后退了一步,瞪圆了眼睛。光头没顾上找碴,目光逡巡一圈,往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走去——傍晚时碰瓷未成年的老太太和另外两个男的就坐在墙角,三个人点了一包小薯条,没有人吃,好像只是摆个造型,脚底下堆着鼓鼓囊囊的行李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