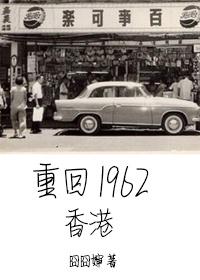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与猫同行快穿 > 第39页(第1页)
第39页(第1页)
他的母亲信道,他也信,所以他“顺其自然”了十几年,今后或许也将“顺其自然”下去。正因如此,他从不强求任何人任何事,包括与程澹的缘分。
“那十年之后呢?”程澹一眨不眨地看着他,心绪复杂,一向清澈的眼瞳也染上了浅浅的雾霭。
“十年之后,你便住在我心中了。”张玉凉点点他的鼻尖,笑道:“届时,你在与不在,都伴着我。”
他记得初见时程澹给予的温暖,记得这些日子相互陪伴的点滴。往后十年,还有更多的回忆会被创造,这么多的美好,足以陪他走完余生。
程澹眼眶一热,忙垂下眼帘,却抱紧了张玉凉的手臂。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明白何为陪伴。
孤独的程澹,终于找到了他的张玉凉。
一如被上帝分开的两个灵魂,终于在尘世间邂逅对方。
张玉凉缓缓俯身,一个吻印在程澹唇上。
……
摊牌之后,程澹与张玉凉的相处方式并未改变多少,他们的生活也依然如之前那般平淡而又充实。
程澹陪张玉凉读书作画,消磨时间;张玉凉照顾程澹的饮食起居,迁就他宠爱他,让他每一天都过得开心。
被张玉凉这么日复一日地捧在手心暖着,程澹的心即使是石头做的,也早就捂热了。
于是渐渐的,程澹陷入了他特意为自己创造的“温柔乡”,仿佛被蛛网束缚的猎物,再也无法挣脱。
当然,他亦不想挣脱。
世上的人,谁不想要一个才貌双全又温柔体贴的张玉凉?他傻了才把人往外推。
安逸的生活总是过得很快,一转眼程澹和张玉凉已经在临初居住了将近两个月,从寒冬到开春,马上就要过年了。
除夕的前一夜,张家连着派来五六波人请张玉凉回去过年,但都被他以年节期间仍要专心读书为由打发离开。
但口口声声说要读书的人,却在打发走张家的下人后拉着刚刚睡醒的程澹贴窗花。
窗花是张玉凉用特意让人买来的红纸剪出来的。花是连枝干一起剪出的红梅,除了花以外,还有很多憨态可掬的小动物,其中最多的,便是程澹猫身的种种姿态,或抱着玉璧呼呼大睡,或拿爪子拨弄毛线团,一个个活灵活现,萌态十足。
程澹嫌弃地挑起一张,左看右看想挑出几个毛病,奈何张玉凉的剪纸手艺太过精湛,他看了许久,竟慢慢觉得这些红通通的小毛团分外可爱。
“张玉凉,临初居好像不是张家的产业,我们随便在人家的门窗上贴窗花真的好吗?”程澹拿着两张剪纸在窗户上比划了一下,突然想到这一点,连忙问道。
“临初居的确不是张家产业,而是我的产业。”张玉凉微笑着说,“几年前,我出资与临初居现在的老板一同建造了临初居,本意是想束发之后能有个读书的去处,没成想短短几年功夫,临初居名气便如此之盛。好在那人一直为我留着听雨阁,如今我们才能在这里躲清闲。”
程澹听得目瞪口呆。
临初居的名气不只在帝都,哪怕放眼整个天下都是赫赫有名的读书圣地,令无数高门贵子趋之若鹜的存在。
不管是附庸风雅,还是当真想潜心钻研学问,临初居都是再好不过的选择。然而张玉凉却说,这不过是几年前他出资与人合办的一处产业。
几年前他多大?有十岁吗?
张玉凉好笑地捏捏程澹的脸:“我自幼丧母,在大夫人名下充当嫡子抚养,故而早早便通晓人情世故,也就是外人说的,早慧。”
顿了顿,他又说:“我一贯不喜张家作派,待得时机成熟,便会搬出去住,临初居只是我准备的众多退路之一。何况,这里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好,那些名气多为人云亦云传出的虚名。”
“原来那个凶神恶煞的夫人不是你的亲生母亲。”程澹放下剪纸,伏在张玉凉膝前,仰面看他。
“母亲年轻时可是岭南第一美人,现下虽芳华不再,却也是风姿绰约,怎能说是凶神恶煞。”抚了抚程澹披散的长发,张玉凉继续剪着半成型的小猫。
“你小时候她是不是对你不好?”程澹脱口而出,问完又后悔戳他伤口,话却收不回来了。
正当他懊恼地想扯开话题时,张玉凉忽的笑了起来:“不,母亲待我不错,鲜少训斥或为难我。”
“你骗人!”程澹满脸的不信,“若她真对你好,为什么你那么小就想着搬出去?”
程澹虽是孤儿,但打小就有人照顾着,没吃过什么苦。在他看来,张玉凉明明有家却不愿呆,一定是受到了委屈,而能让他委屈的,阖府上下只有他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