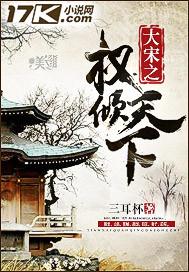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臆想情人abo dilemma > 第44页(第1页)
第44页(第1页)
站在后面的人这才走了进来,随意地拽着老管家的后衣领,把他拖了出去。
临走前,又卡住了季川的手,轻笑着:“别啊,那么好看一张小脸,打残了多不好啊。”
“你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可以,”男人又发出一声轻笑,“和他谈谈你的理想,对不对?”
季川古怪地看了一眼男人,无所谓地耸了耸肩:“你打的什么主意。”
男人不理他,兀自走了出去,季川犹豫了一会,还是蹲了下来。
“啧啧啧,小脸蛋都哭花了,”他摆正了岑漠的脸,给他看一张照片,“是不是很委屈?可惜,是你打破人家家庭和谐的呢,落到这份地步,也是活该啊。”
岑漠眯着眼,好一会儿才看清了眼前的画面,照片上池怀霖全身赤裸,搂着季川的腰,从背后吻着他,而眼前人以胜利者的姿态,轻蔑地俯视着他,把照片扔在他脸上,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股恶心的感觉越发明显了,他干呕着却吐不出东西来,胃绞痛得难受,头像被电钻钻开。
——原来池怀霖不是属于他一个人的臆想。
他不知道悲伤从何而来,也不知道驱使着他爬起来的力量是什么,屋子的外围已经燃起来大火,是从那片薰衣草花田开始的,他拿湿布捂着口鼻,四肢并用地爬了出去,脚却在跨出大门时感到了一阵电流,让他条件反射地缩了回去,铁栅栏从两边迅速地合上。
岑漠看着眼前缓缓合上的黑色栏杆,突然笑出声来。
他从来,从来就不想,让他出去过,要把他关在虚无缥缈的梦里。
哪怕他那么乖,那么听话,那么顺从了,他还是不爱他。
或许是苍天有眼,门在差一条缝的时候,因为大火烧到了这边而卡住了,岑漠扶着门站了起来,滚烫的铁门烧得他手都冒青烟,他把那双他开心了一整个月的鞋子踢掉,赤着脚走出了门外,再忍着剧痛把大门紧紧合上。
少年看着陌生的路,从缓慢行走,到逐渐加快脚步,最后终于跑了起来。
粗粝的石子划破了细嫩的脚,跑到外头的时候,每一步都是一个血色的脚印,少年却不知疼痛地朝前跑去。
他想起那海底的小美人鱼,拿声音作交换,走在陆地上的每一步,都像刀割一般疼痛。
就像他此时此刻,大张着嘴也无法言语,十一月的冷风灌得他喉咙生疼,他从荒野跑进繁华里,浑身都是血的腥味。
他以前曾经幻想过,终究会有一天,他会走出那个幽深的病院,和爱他的人一同去看海,去捡小贝壳,去晒味道好闻的阳光,去跳进无边无际的海里,拥
抱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