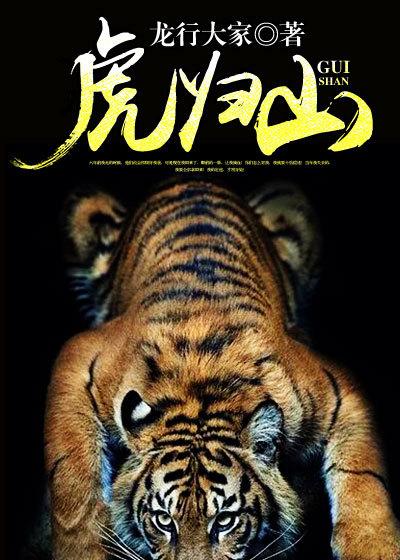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帝后耕耘记(康熙与孝惠)女主第几章怀孕 > 第45页(第1页)
第45页(第1页)
布木布泰的手生疼,那是被一个即将死去的人用着最后一次能量抓握的疼痛,是肉被指甲无情穿破的疼痛,更是对她所有生命存在意义的无情否决的疼痛。布木布泰哭了,她突然间觉得绝望与悲凉。这一生,就是如此的毫无意义吗?前半生为了一份不可靠的感情,后半生为了一份自以为的誓言,为男人、为儿子、为大清——可是谁来为她呢?为她呢?!布木布泰从未有如此的绝望。当年皇太极离她而去,她又何常不悲伤?可她并没有多少时间来悲伤,就要为着那誓言为着才六岁的儿子谋划。如今呢?如今她就可以悲伤了吗?布木布泰突然睁开了哭泣的泪眸看着儿子。那是张没能闭目的出着痘子的脸。谁是对你最好的人?不是我吗?……只有我——只有我会不顾着自个儿的身子整天坐在你的床沿,给你喂食,给你抹汗。布木布泰并不在乎这些可怕的痘子,用着指腹一点点的给儿子整着面儿,额头,眉骨,鼻子,脸颊,下巴。只有我对你是真的好啊儿子,可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布木布泰直视着那双仇视与诅咒的双眸,这一刻,突然长升出激动来。你要看吗?要看着我死吗?……呵呵,好呀,你看着吧……总有一天,我能再造一个大清的帝王,我能成为这大清最伟大的存在……你去吧……去吧……去守着你的女人……我布木布泰——不需要你这么没用的儿子——太后理了理面颊儿,再整了整衣装,站起来摆了摆,定了定眸光:“来人——大清顺治帝——驾崩。”最后两个字儿,很轻,苏茉儿在外寝几乎听不真儿。她进入内寝,还是看到了从小看着长大的如今也仍年青的那个少年天子,却被那仇恨的目光吓得退了两步。她也是随着太后风雨间几十年走过的老人了,什么是没有见过的?太后已经走出了内寝,指使着奴才。苏茉儿想了半天儿,还是趋向前近了内榻,伸了手儿抹过顺治大张的眼帘。福哥儿,安心去吧,腾格天总是会保佑你的——顺治正月初九,爱新觉罗玄烨即皇位,史称康熙帝。蜗居顺治十八年二月。永寿宫里的奴婢们正侍侯着新的万岁爷原来的三阿哥试着那新做成的小龙袍。宁芳歪在外榻上看着:“还是穿红色的好看,这黄色乍眼。”玄烨听了,低了观察了一番衣袍。“我的主子,只有皇上才能穿着明黄的色儿,这可是独一份儿的,呵呵,您看这不挺精神的。”宁芳虽听了容婆子的话,却不苟同:“可这黄色的确没那降红色精神嘛。”宁芳见小三穿好了,便摆摆手让他近了前,摸了摸龙袍的料子,绣线细若不见,面料软滑,“这料子好好,哪来的?”“回主子,是打南面苏、杭进的织料,太皇太后见着好,便让做了龙袍,绣娘也是南面来的。”李德全晓得这事,便回道。“难怪,这手艺可比宫里的强多了。”“宫里还有,给你赶着做几件新装。”玄烨见她喜欢,便给了李德全眼色。“不用了,料子虽好,我也用不上,衣服还多着呢。到是有那上好的白绸什么的取了点来,赶着没到夏日,做了寝衣才好,那衣料子清凉。”“嗯,我知道了。等会要去皇玛嬷那,怕是要留了饭,你就不用等我了。”“哎——,真没意思,又一个人吃。”玄烨依了她坐下:“最近也是忙得直转转,再过几日便好了,再陪着你好好吃饭。”宁芳见他讨好的样子,也没怎么生气,便笑着道:“知道了。知道你是真忙。”理了理他的衣襟,“不管是好不好吃,总要多吃点。我这里不用你操心,一屋子人呢。”“嗯。”玄烨上打遛子就靠在了宁芳肩上。“……你快要搬进清宁宫(即保和殿)了,我是不是也要搬出永寿宫?”“按例是的。不过慈宁宫有皇玛嬷与众位太妃住着,也没什么地了,皇考的遗妃也不太适合住在那里。宫里的地方虽多,能住人的地方也就慈宁并后宫几处,其他都年久破败,一时也住不了人。”“那就不用搬了吗?”“你不想搬吗?”“也不是,哪还有太后住在皇帝后宫的道理。不过,我可不想同那么多人住在一起。你看看给我寻所独立的院子,不要像永寿宫这样被围着的,最好是靠墙。不用大,还是这么些人就可以了。嗯——最好能离了那些人远远的。”“……嗯,我找找。”太后听了那太监的禀报,气地脸颊儿发抖。苏茉儿遣那太监出去,正想安慰几句,外面便报了皇上驾到。当小皇帝坐于榻前,太后已是一派常色。“几位太傅那里可还照常?”“一切如旧,孙儿并无改动。”“嗯,你如今岁小,于朝事知之甚少。朝里又有四位顾命大臣看抚着,到是不太打紧。只是即登了基,便当越发专于朝事,那些奏章折本还是要日日看的,不懂的——可以不开口,私下里再问不迟。”“是,孙儿明白。”太后与康熙幼帝相互间又说了些话,直到快近传膳。“皇上,那宦官吴良辅与官员相交贿赂勾结,本是死罪。但为先帝所护。可他’变易祖宗制度‘是为事实,怎可因一己私心护那孽畜。”“孙儿明白,定当按律令于以严惩。”“嗯。皇上,你也当引以为鉴,切勿以私视国。”玄烨嘴上虽不差偏离地谨遵,脑子里却疑惑,不过是个太监,再受皇考宠幸也是案板上的死尸,不过是时间的问题,何需皇祖母亲视?二月十五,诛有罪内监吴良辅,罢内官。“呵呵呵。”太宗懿靖大贵妃娜木钟笑得爽快,“气死了儿子,到如今偏要找个太监的不快。本宫看,这布木布泰也是老糊涂了。”康惠淑妃巴特玛微而一笑,把玩在眼下的杯子:“她不是老了。只是迁怒罢了。”“呵呵,也难怪的,刚同她那死儿子缓和了关系,却叫吴良辅的一纸密奏气死了儿子,哈哈哈……真是有趣的紧。”巴特玛放下了杯子:“这事也就过去了,以后也别提了。布木布泰毕竟不是善角。”“呵呵,我知道。不过说了又如何?还不是被我们算计了。”娜木钟并不在意。“十次里算计了她三次去,并不容易察觉。不过,旦凡做了总会留下些顺头儿,布木布泰的厉害你我又不是没见识过,何必过了。”娜木钟打量了巴特玛,还是柔善、慈和,却淹有细腻无二的心思。这次,若不是她提醒了自己进上吴良辅这张废牌,也不会这么痛快的扰了那母子的和气,真算是为博果尔报了些许的仇。娜木钟平静了心态:“妹妹这次——想姐姐怎么谢你儿?”巴特玛笑得温良:“没什么的,我不过是觉得闷了,想找那么点乐儿。”娜木钟看着她那眼色,就如同在说“今天天气不错,要是能下点雨就好了”的样子,心下却是一颤。不过也没什么,反正也没什么可失的了。“那到是要谢谢妹妹了。”“姐姐何必客气,我们做姐妹也不是一两年了,从林丹汗时到伴着太宗左右,也算是最亲厚的了……妹妹与你可不同,身边一直没个亲人可以说话念想的。见了能让姐姐痛快的自然要讨了姐姐开心的。”娜木钟见巴特玛嘴边那沫子笑,抖了抖面颊子:“妹妹——就真的敢?”见她仍是带笑回望着自己,“她毕竟是太后,若是真被她抓着了,我也没什么可牵挂的,可你——”“呵呵,姐姐说笑了,我有什么可挂心的?……再说了,妹妹我可例来守规纳律不曾有丝毫错处了去,她又凭什么找了我的晦气?”娜木钟心下哼了一声,到如今才算是明白这么个人,是掩得深了。深夜,李德全端了汤水进来,见皇上仍对着那张宫里的地图细琢着,便放了汤盅子给皇上盛了一碗。“皇上歇歇吧,太后主子使了人傍晚给送来的,补气的。”玄烨接过了,边想边喝着,便看向李德全。“清宁宫收拾得如何了?”“再有两日即可了,请了太后示下,折个好日子便可迁往。”玄烨又举了图,直盯着一角儿。“皇上,可是为主子选好了住处?”玄烨瞅了他一眼,并不作答。“皇上,这宫里宫规戒律一条条的,若是没个典章律条的,怕主子也是不能住的离您太近。”“……哦?你有什么主意?”“皇上,奴才没读过书,自然是寻不出什么章法来了。”玄烨见那他直向自己打眼色,突然明白过来了,便是一笑:“也难怪你这个奴才得皇额娘喜了。行了,是个机灵的。”“呵呵,那还不是主子与皇上给奴才机会。”玄烨也不同他多言:“明日传旨,宣中和、保和、武英等殿大学士午后入内授业,凡有出众者留授于朕。”“喳。”一晃数日,日头渐落,新登基的康熙帝进了慈宁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