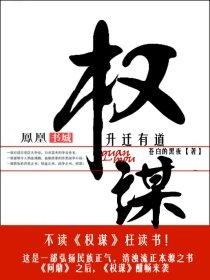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雁声来古言1v1免费阅读 > 蹲大牢(第2页)
蹲大牢(第2页)
已是正当夏的时节,晌午的日头如炭火烤得人滋滋冒汗,码头的脚夫光着上身卖力气,一身腱子肉晒得黑亮油光,脸黑得打远分不清眼睛鼻子,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
刘二扔下肩上的麻袋,擦汗的间隙往河边树荫下送去一眼,他大哥面前站着个白净公子,那生得,他长这么大头回见着这般貌美的男子,身姿跟谪仙儿似的,哪哪儿看着都不像是和他们有话可搭的人。
刘大弓着腰身,酡红的脸上顶着讨好的笑,“公子您有话直说,凡是我知晓的定不藏着掖着。”
“四个月前的某一日晚上,你们兄弟两人曾帮郁姑娘抬一人上山,你可还记得是在哪处地方?”
闵宵的话一出,刘大酱黑的脸上瞬间显出几分惨白,八月的天里凉气顺着脚跟爬。
他抓头挠手眼神飘忽,“这这四个月前的事,记不得了,记不得了”
闵宵将他的心虚怕事看在眼里,直言道:“我是那日你们抬的人。”
刘大瞪直了眼,正主找上门,他再多推诿岂不是将自己往火坑里推,冤有头债有主,本就不是他兄弟二人有心害人。
“公公子,我兄弟二人只是拿钱办事儿,我们不晓得那日要运的是活人,等到了地方,那郁姑娘说是她不着家的夫君,谁承想她谎话连篇,这事儿真怨不得我们兄弟,要是早知道定不会贪那亏心钱”
他一边说一边觑这公子的脸色,只见他面上怔愣,倒不似生气,花瓣般的眼皮儿微微颤着,也不知是拨了他哪根心弦。
半晌,他似呓语般喃喃:“她说我是她夫君”
刘大不明所以,“诶!是啊,正是她说绑的人是她夫君我们才没报官,清官难断家务事嘛!谁承想她是撒谎害人,公子若是需要证人,我兄弟二人定当仁不让的!”
闵宵收敛心绪,正色道:“不必,她没有害我。你们可知她住在哪处?”
刘大挠头,这两人莫非真是闹了脾气的小夫妻?怎的连自家住的宅子都找不着地方。
但他未多嘴,只摇头道:“郁姑娘的家极偏,下山时顺势就能走出来,可上山时曲折弯绕的,几十上百条岔路,也没个正经大路,且那处山多,出来了便找不到她住在哪一座,须有人领路才行。”
对面的人半晌未作声,他试探问道:“公子?”
闵宵垂下眼睫掩盖情绪,“多谢。”
“那我走了?”刘大见无事发生,心里松快起来,嘴上打溜儿似的碎碎念叨:“还以为您是哪家官老爷来找我盘问呢!这城南冯府的老爷遭了黑手,小半年了还没寻着凶手,许是见我们码头的汉子粗壮,官差日日点卯似的来找我们盘问”
闵宵未多在意他的话,那声音飘进耳中转了一转,直到他转身走出几步,脚下突然一顿。
几息过后,他才又迈步离开,步伐匆忙了些。
城西杂货街摊贩林立,有处曾氏典当行租了铺面,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的女子,在此处开了二十来年的店。
“曾姑娘。”
面前响起一道清朗的声音,曾姑娘自账本上抬眼,视线落在来人身上,顿了一顿。
好一个俊俏公子。
“客官是要典当何物?”
闵宵将银票压上桌案,“我找人办事。”
曾姑娘看了几眼,略一挑眉,年纪轻轻出手这般阔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