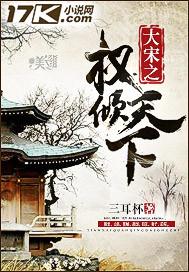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东窗计古言1v1密码本 > 第三十四章难追(第1页)
第三十四章难追(第1页)
总是想信的,想信至少她那份情是真的。却像是重重山隘,陈怀只觉得疲惫至极,不敢再走。若是细想来,当下她未曾害过他什么。可从她口中说出来的话真真假假,他是一概不知道要如何处置了。他咬着她的肩颈,寸寸透骨。“五年前为何骗我?”总要一件件说清。纪盈低眸,坐在桌上轻晃着腿失神:“江生岭要挟我,他怕你取代了他的禁军官职,让我逼你出京。”“他拿什么要挟你?”事关姐姐,她不能说。纪盈摇头,得了他一声冷笑。他又问起她救出那探子为何还要打晕他把他送回到自己手里,纪盈照实答了,陈怀没有再追问。“偷令牌的事,我是察觉到江生岭在耍我,所以干脆挑明。他歪心思多,我也怕他……对你不利。”纪盈歪着头,用自己的耳朵轻轻贴着他的耳。陈怀也不再问了,他恍然觉得自己听了那么多个字,人生头一次失去了所有的判断,对错是非,一概看不明白了。多问徒劳。他深吸气缓和下来,拳头砸在桌上:“你和金遥迢一同去巡视军营的事我已知晓。知府决断,他们同意了,我也不好反对。一个半月,你回来之后就立刻回京,我大抵要两月才归,不必见了,我会让人把和离书送到京城。你被我发现,已经是颗弃子,就这么跟你的上级说吧。”纪盈心揪在一处,看他要离开,猛地拉住他,颤着声音保持着冷静:“暂且,不要和离,不要休妻。你带着兵去堵江生岭的事,他碍着我不会上报,等到事情过去了,他也不会再提此事,现下不要推开我,免得你惹火上身。”“他倒是在意你。”陈怀背对着她轻声说。“他不是在意我,他是在意……”纪盈闭了口,闭上眼,拉着他的手也无力。被他禁锢着腰身撞到墙上时,恍神片刻纪盈便懂得他想做什么。裙摆被轻易撩起,还未曾被解开的衣物隔着那发硬的东西顶在她身前。“既然你为他逼走我,他为你敢欺瞒圣上,你们到底在玩什么花样?他知道你在床榻上是什么样子吗?”五年前那股要报复她的情感又重燃变得强烈,用这种事来凌辱她似乎是最合适的,她总是在骗情爱。他看惯了这世道上的人是如何践踏与被践踏,这样的事也不少见。但总是看到她眼里些微慌乱无措和伤怀,便不能再动。他终究不想变成少年时见过的随意践踏别人的人。“陈怀。”她落不下泪,裙摆之下逐渐寒凉,本来熟悉的距离却显出了陌生。“你真的记恨我,想罚我,把我拉出去打军棍,游街都好,”她看他没有接着动作,知道他也没那么决绝便接着说,“别拿情爱的事羞辱我。”所有情爱,她要的是真心,不是报复。至少不要拿这件事惩罚她。他闭着眼:“你去和金遥迢会和,我会派席连跟着你,这一个半月你休想再惹出任何事来。”她眼底死灰一片,他放手之后,她缓缓从墙边滑落到地上坐着,看着他留下的微微晃动的门。
“喵”五里摇了摇尾巴从窗口翻进来走到纪盈身边,跳到了她怀里。“我可以骗他的,”纪盈吹着窗边风,冷出了几分清醒,缓缓抱起五里和它对视,“我可以骗他,那双鞋不是我的脚的尺寸,是有人故意陷害我。我可以说那是我做下的想着多塞些毛绒故而留了空,不知被谁偷了。我都可以说的。”五里两只前爪被她攥住,一滴泪突然落进它的毛间。“可我不想骗他了。”她抱紧五里坐在墙边,决堤的情愫与泪水才涌出。莫名的,一身轻松,她不必也不会再瞒着他什么,不需再胆战心惊。但他也不会回来了。彻夜无眠,纪盈把眼哭得半肿,喜雁给她梳妆,蹲在她面前睁着眼默默不语许久。“别担心,我没事。”纪盈揉了揉喜雁的头。“姑娘,你来这儿之后总是不高兴,事情之后咱们还是回京待段时日吧。”喜雁给她擦手。她点头。这日子终究要过下去的,纵然此时此刻,心如刀绞,从未停歇。管家给她牵马来时,才说陈怀清早就已经出发去军营了。纪盈回首看着定期烧埋的杂物堆里,露出边角的那几双鞋,嘴角微动,敛眸转身也不再多看。纪盈从鸢城带了百人左右去与金遥迢会和,大多数的人还是从金遥迢所部抽调的。席连看破那双鞋时,再见如今纪盈这副样子,也猜得到这背后的七八分事,一路上仍旧恭敬,并不多问半字。“此次要去的叫连城,离金遥迢的定远寨都有八日的路。连城地处偏北边境,当地驻军是沂川府所有,守城之将五日前战死,新将还未任命,暂由副将补任,”席连说着,看了看纪盈虽颓靡但还在听便接着说,“连城乃是大炎南下最关键的城池之一,若破,身后五座城池皆无守力,故而关键之际。”也便是如此,那副将称连城军心不稳,才紧迫要来处置。听到一阵杂乱马蹄声,纪盈回头看到一阵烟尘,而后群马和人影才清晰。“金遥迢到了,我们先进连城吧。”她看清了来人说道。该说这金遥迢是个什么性情的人,自上回的事后,再见纪盈,一下了马马鞭都没放下就把纪盈的肩给勾住。纪盈顿时以为自己回到了京城,哪个狐朋狗友又勾着她上不清不楚的地方。“安夫人和小公子的事多谢你了,”金遥迢笑,用马鞭戳了戳自己的头,“你怎么脸色这么差啊?”纪盈苦笑:“临走时跟陈怀吵了一架。”“为上回我做下的事吗?”金遥迢一拍腿,“我去解释吧。”“不是……”“那……”金遥迢眼尖看到纪盈脖子处微露的一道齿痕,叹说,“还说你们房事不协,看起来挺激烈的。”----五里:你也不怕拿我擦眼泪迷眼睛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