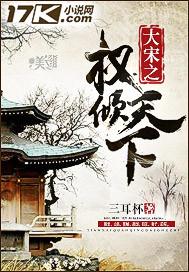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蒋经国传江南epub > 第27页(第1页)
第27页(第1页)
一九四七年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和一九四八年的副总统选举,即是测验三青团功能的温度计。蒋介石的原意,副总统一职,内定孙科,他对桂系的实力,始终存着戒心;但当时担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德邻(宗仁),并不怎么唯命是听,一场攻坚战,在首都展开。三青团名义上并入国民党,而各县市党部的主委,由担任;副主委则由三青团分子出马。和三青团,势不两立,而三青团内部,尚有复兴社、太子系的激烈对抗。大部分国大代表,出身各地三青团,党中央下令支持孙科,孙科应稳操胜券,轻易击败对手李宗仁。结果,李宗仁得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孙科仅一千二百九十五票.[4]李胜孙负。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如白瑜[5]、周天贤.刘先云、许伯超等,宁置贺衷寒、袁守谦的劝阻于不顾,也要支持李德邻顺利当选。李、孙一役,经国歉疚,蒋先生伤心,国民党的腐朽,差不多已无药可救。青年团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经国转为党的中央委员[6]兼中央干部训练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为张厉生。官衔又长又大,职权无足轻重,经国对这张冷板凳,当然就兴趣索然。好在,党的职务并不重要,他尚担任预干局的中将局长,为国防部的一级单位。预干局的全名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一九四六年成立,和它平行的是“‘国防部监察局”,局长彭位仁,经国推荐。彭投桃报李,用的全是太子嫡系,所以“外界把监察局视为预干局的盘支。”[7]抗战末期,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大前提抗战建国,还我河山,所以一呼百应.志士来归。“剿匪”是内战,性质、内容、时机和抗日战争,好比地球到月亮的距离。也许内战方殷,蒋公出乎情势需要,顾不了那么多,旧梦重温,炒第一次青年从军运动的冷饭。预干局成立的首件大事,召集青年军干部会议,黄维[8]、刘安琪、钟彬、覃异之等将领,纷纷赴会。会议通过征集第二批青年从军,报请国防部批准。蔡省三先生,偏偏另持异议,他说:“问题是抗战刚刚结束,国军正在裁减整编,第一期青年军的复员安置,尚未竣事,许多地方都被‘青年从,扰攘不宁。现在忽然又来搞个‘青年从军运动’,实在是‘师出无名’,不切时宜。要象第一期那样,拼凑一个‘征集委员会’,势不可能。‘运动’眼看是搞不起来,于是只得作为国防部改制后的一项措施,通过行政命令来办理。由预干局会同兵役局,在全国各地‘招兵’,名义仍然叫‘征集知识青年从军’,并公开宣告,入伍后系接受‘军士’的预备干邵训练,成绩优异者,可保送升学‘军官学校’,或直接晋升军士,将来可按役龄再晋级军官。这就是以升官’为诱饵。尽管如此,但是知识青年应征者扔旧为数寥寥,随后是来者不拒,文盲也收,流氓地痞,一并收罗。勉强凑数,虽然兵不足额,仍然恢复了二0一师到二0八师的八个师的建制。好歹总算让这支嫡系武装延续了下来。”[9]第二期的青年军,没有第一期幸运,战局吃紧,先后被调到前线参战。结局,或残或俘,到上海失陷为止,兵员建制,荡然无存。马歇尔使命(arshalission)宣告中止,国共双方再没有借和谈假惺惺作态的必要。诚如陈立夫所说:“国民党的天下是打得来的,谈是谈不去的。”国府委员会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八日下总动员令,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则发动夏季攻势为回应,东北、热河、冀东各个战场,展开战略性反攻。实质上,谈谈打打,战火燎原,从日本投降那天起,任何一方都没有住过手。初期国军以兵力武器的优势,略占上风。几经交手,所谓“美式装备”的国军精锐,不过是银样蜡枪头。试看,毛泽东下列举证。他说:“第一年作战(去年七月至今年六月)歼灭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伪军、保安队等杂部三十四万人,共计一百二十万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给予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兴奋了全国人民,莫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10]毛泽东承认.共方付出三十余万人伤亡的代价,和大批被敌占领的土地,但是,共方立于主动。孟良崮,[11]国军张灵甫殉难,莱芜战役李仙洲被俘,两役约十万人被歼。鲁西南战役,国军四师九旅之众,遭到歼灭。国军大书特书的一场胜仗,是胡宗南的部队,攻入延安。[12]但是换取到的,不过一场空欢喜。津浦线短暂通车,陇海西段,又被刘、邓大军所切断。战场上国军频频失利,共军的新战略.执行“外线作战”。以乡村包围城市,由游击战,扩大为阵地战,“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国军变强为弱,变攻为守,双方形势消长,急转直下,连西方军事家,都为之不解。其它方面,如政治、经济、精神、心理,[13]和军事一样地令人沮丧。导源于“沈崇事件”而爆发的反美学潮,迅速蔓延全国,学生罢课、游行、示威,了无宁日。他们提出的口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无不矛头对准南京政府,旨在瘫痪国民党的后方,打击民心士气。毛泽东称此为“第二条战线”。国民党当局,自然很清楚,这是敌人的恶作剧,是中共地下党幕后的策动。经国负责的三青团组织部门,的确绞过脑汁,派精英分子,渗透到各学校,从事各种防范措施,或壁垒的明地,相互对抗,可惜成效极其有限。国民党人,即使在后方,也不是中共的对手。经济方面,通货膨胀,生产萎缩,加上庞大的军费开支,公教人员生活,日益恶化。政府财源枯竭,唯一的希望,等待美援,美援不来,只好滥发钞票,借资挹注。失业、饥饿、萧条,每一项因素,分别困扰着国民党政府,加上中共巧妙的宣传,轻易地转嫁到另一方去认为蒋介石集团,独裁卖国,贪污腐化,反正一无是处。国民党若干短视暴虐的举措,[14]无形中亦丑化了自己,帮助了敌人,加速崩溃的步伐。经国当时在南京的地位,相当微妙。一只脚在党里,一只脚在军里,可都算不上高层决策人物。特务组织,“军统”和“中统”,没有他的的,各军种各兵团,直属参谋本部,鲜有轮到他插足的余地。大局如斯,经国对一切的情况,看得比他父亲还要清楚,原因,蒋先生高高在上,很少有兼听的机会。经国因而忧郁仿徨,口头上、行动上,他要扮演成乐观坚强的斗士,强调“天下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心灵深处,阴暗深沉,看不见地道那一头,有任何光芒。扶撑危局的办法,集南京所有的诸葛亮,也提不出什么锦囊妙计。即使有,蒋先生那样的性格也听不进去。听进去的,办不办得通,尤其成问题。避免坐以待毙,一九四七年的秋天,经国召集亲信反复研究,且得到蒋先生的首肯,终于提出一个对付中共的新方案—建立“实验绥靖区”。[15]纸上谈兵,计划是不错的。绥靖区实现全民武装,把及龄壮丁,全编成“戡乱建国义勇队”,荷枪实弹,保家保乡,巩固收复区,根绝共军兵员粮食供应。预备在江苏、安徽、河北、河南、湖北、山东六省,各划专区试点。“中央训练团”,特别开办“实验绥靖区干部训练班”,训练区长、县长等干部,配合施行。认真实施,也就和美国在南越办的战略村类似,是以组织对组织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