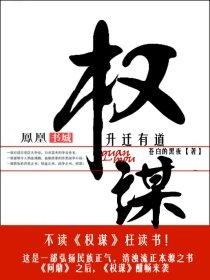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何处是归途图片 > 初夏(第2页)
初夏(第2页)
那药物的其中一个副作用,是会引起情绪抑郁,何况他早就有过自毁的念头。
"一厢情愿也好,填不平的鸿沟也罢。这一次,不要再离开我了。"他又说,握着她的手搭在自己手臂上。
他似乎还想说什么,动了动嘴唇,却终究没有说出来。
他的短期记忆力也开始受影响了。从他们下车,一路慢慢走到这里,他这样突然想不起来要说什么,已经是第二次。
谢情苦笑,"你把我看得这么紧,我想离开你都难吧?"
"那是因为我知道,你不会留下来。"程拙砚说,"就当是我自私吧,我做不到看着你走。"
他们在春日的河岸漫步,四下无人,只有一阵阵温暖的风,吹落一地或粉或白的玫瑰花瓣。玫瑰园似乎打理得不算太精心,半人高的花树下,颇有些杂草和淡黄的野花,还有些雪白的蒲公英。
谢情弯下腰摘了一朵,用力一吹,看着雪白的小伞在暖洋洋的风里洋洋洒洒地飘往莱茵河上去。
"喏,给你一个。"谢情又摘了一朵大的递给程拙砚。
真是非常漂亮的一朵蒲公英,毛绒绒,圆滚滚的,在春日的暖阳下显得柔软又可爱。
程拙砚没有吹,只是出神地看了很久。
他的手指有些微微发颤,连带着蒲公英的绒毛也跟着微微颤动。
"蒲公英不是拿来看的,是拿来吹的,"谢情说,"你们这些有钱人啊,难道小时候连蒲公英都没玩过吗?"
他笑了笑,说:"不让。"
"这都不让?那今天让了。"谢情拉起他的手,举在唇边,"吹吧。"
程拙砚却依旧没吹,目光从蒲公英上转到谢情的脸庞。
她脸上泛着红,微微出了一点汗,兴致其实并不算高,可是看起来还算愉快。
就像往常一样,不论他带她去哪里,喜欢不喜欢,她总是尽量放开心怀感受一切。
对了,她说过,这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很叫他羡慕。
"小情,上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对你说的话你还记得么?"他问。
谢情记不得。
他们上一次见面,是她被他逼急了,一枪把他崩进医院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说了什么?
尽是些疯话吧?
程拙砚不以为意地微笑,"你又不记得了,是不是?你总是不记得。到底是因为记性不好,还是因为从来都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谢情被他问得一愣,没说话,欲盖弥彰地转过头去看河上的游船。
"我那时候说,我愿意死在你手上。"他语气这样平静,仿佛只是再说一句最最无关紧要的话。
谢情本来心里就有些抹不去的罪恶感,听了他的话,骤然回头看他。
程拙砚却又移开了目光,轻笑着,用力将那一朵蒲公英吹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