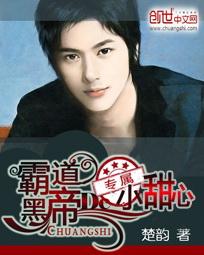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芈月传69集免费观看 > 第64页(第1页)
第64页(第1页)
便是这等郭外之郭,也是有些酒坊与赌场的,越是生活在底层的人,越是需要这些场所来麻醉自己,忘却痛苦。黄歇停在一间酒坊外,凝视半晌,走了进去。里面熙熙攘攘,多是些底层的军中役从与混迹市井的野汉,也有一些落魄流浪的策士杂坐其间。黄歇这一身贵公子打扮,倒与众人格格不入。那跑堂见他气宇不凡,忙从人群中挤出来先招呼了他,点头哈腰道:“公子,请上座。”黄歇跟着他的引导,走到里间坐下。便有掌柜出来问他:“公子要什么酒?”黄歇看那掌柜半晌,从头看到脚,才点头道:“要一壶赵酒。”掌柜怔了怔,左右一看,压低了声音道:“公子如何知道小店有赵酒?”黄歇却微笑道:“我还要一份熏鱼。我有一位故友,向我推荐过你们这里有邯郸东郭外熏鱼和燕脂鹅脯。”掌柜的脸已经僵住了,只机械道:“是!是!”黄歇坐在那儿,看着那掌柜仓皇退下。不一会儿,便有一个布衣文士自内掀帘出来,走到黄歇的席上坐下,他身后的侍从迅速送上黄歇刚才点过的酒肴。文士端起酒壶,倒了两杯酒,送到黄歇面前,笑道:“这家的酒不错,公子也是慕这家的赵酒而来吗?”黄歇端起酒杯,轻尝一口,笑道:“果然还是上次尝过的味道,看来我并没有找错地方。”文士脸上的肌肉抽搐两下:“公子如何知道这里有好酒?”黄歇摇头道:“我并不懂酒,只是上次在城内一家酒肆,有位朋友请我尝过那里的赵酒,还有熏鱼和鹅脯,我觉得很好吃。不过那家店不久之后就关了,没想到搬到这里来了。”文士笑容一僵:“公子又如何知道这店搬来了此处?”黄歇向内看了一眼,微笑:“我那位朋友走到哪里都会留下踪迹,我跟着他的踪迹过来,就能找到。”文士连笑也笑不出来了,眼神不由得顺着黄歇的眼光看向内室,立刻又转回来,强笑道:“您那位朋友也是赵人?”黄歇道:“是啊,他也是赵人,阁下也是吗?”文士摇头道:“不,我不是,我是中山国人,不过我以前也曾在邯郸住过。”黄歇道:“哦,这家店你常来吗?”文士道:“是啊,所以可以给公子推荐一些他们家的招牌菜。”黄歇道:“嗯,但不知这里的羊肉做得怎么样,我以前在义渠草原上吃过一味羊骨汤,味道真是不错呢。”文士脸色大变,佯笑道:“公子如何会在赵国风味的酒家,点起义渠风味的菜肴来?”黄歇道:“是吗?我还以为这里有呢,看来我得去城外的义渠大营拜访一下了。”文士拱手站了起来,失声道:“公子,您、您……”黄歇微微一笑,忽然内室帘子掀开,那掌柜走出来,向着黄歇行了一礼,道:“公子,鄙主人说,他刚要杀一只好羊,炖一锅好羊骨汤,欲与公子共尝。不知公子可有兴趣入内,与鄙主人共分一只羊腿。”黄歇看着那掌柜,忽然一动不动,良久才道:“贵主人何以见得,我会愿意和他共分一只羊腿呢?”那掌柜的赔笑道:“鄙主人说,公子家前不久也遭了事,公子如今来这里,不是要和人分羊腿,难不成还帮助他人打劫自家不成?”黄歇忽然笑了起来:“我不要这只羊腿,但是,我想跟贵主人说一声,天底下不止一个聪明人,让他好自为之吧。”说完,便站了起来,向外走去。那文士也站起来,与那掌柜面面相觑,眼看着黄歇头也不回,出了酒肆,骑上马往北而去。那文士脸色一变,疾步入内,向主人行礼道:“主父,不好,黄歇此去,会不会暴露我们的行踪?”赵雍冷笑一声:“他不会的。”文士一怔,不解:“何以见得?若是如此,他来这里是什么意思?”赵雍却皱着眉头,掐着指尖推算,半日,放下手点了点头:“好个黄歇,好个黄歇,果然是聪明绝顶之人。这是所谓旁观者清吗?他竟是一开始就没往城里找,而是因虎威之事,直接从义渠大营推断出我们所在的方位来。”他瞄了那紧跟着进来的掌柜一眼,冷笑道:“他怀疑寡人在这里,所以试探于你。而且提醒我们,他已经怀疑到义渠人的事情与我们有关,那么别人也一样会怀疑到。”文士道:“他对我们是好意还是恶意?”赵雍冷笑道:“如果那个女人有生命危险,他会去救她。但为了楚国,对秦国的王图霸业,他是一定会想办法破坏的。因为如果秦国出事,楚国就可得以喘息。”黄歇一路疾驰,来到义渠大营之外,却不入内,只驰马一圈,又去了附近一座小山丘上,坐下来,取出玉箫,缓缀吹奏。过得不久,义渠大营中一匹马疾驰而出,直上小丘。义渠王下马走到黄歇身后,只叉手站着,也不言语。黄歇亦不理他,一曲吹毕,方站起来向义渠王拱手为揖道:“义渠王,好久不见了。”义渠王有些敌意地看着黄歇,问:“你来做什么?”黄歇道:“秦楚和议,我陪太子人秦为质。”义渠王哼了一声:“楚国的人都死光了,非要你来不可?”黄歇道:“我知道你不喜欢看到我,我也不喜欢看到你。但是,今日我却是非要见你不可了。”义渠王道:“你见我何事?”黄歇道:“你是草原上高飞的鹰,她是咸阳宫中盘踞的凤凰,你离不开草原,她也离不开咸阳。我曾经以为,你的到来至少能够让她不再孤独,可如今我发现我错了,你的到来让她陷入了无奈和痛苦。”义渠王大怒:“你的意思是,你如今还要与我争夺她?”黄歇摇头:“不,我与她已经不可能了。但是你再留在咸阳,却只会伤害于她。你的人乱了秦法令她的威望受损;你的骄傲让她陷于你和她的儿子中间左右为难。你若真的爱她,就当放手成全于她。”义渠王冷笑道:“别拿你那套狗屁不通的东西来说服我。你是个懦夫,不敢承担起对她的爱,丢下她一个人逃掉了,让她伤心孤独。她是我的女人,我是不会放手的。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有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江山,谁也无法把我们分开!”黄歇道:“那子稷呢,你就没有为他想一想吗?”义渠王道:“他既然不想与我做一家人,那我就与他分了营帐,也不算亏欠于他。而且他的父亲有太多女人、太多孩子,我不信在她的心中,那个男人的分量会比我们父子三人更重要。”黄歇看着眼前这个自负的男人,心中无奈叹息。眼看一场悲剧就要发生,可是他却不能说出来。他此刻到这里来,也是尽最后的努力去阻止对方。只不过对方明显没有打算成全他的努力。他摇了摇头,道:“你错了。”义渠王冷笑:“我错了什么?”黄歇凝视着他,缓缓道:“你现在走了,还能够保全你自己和你的部族。”义渠王哈哈大笑:“胡扯,你以为,她会对我下手?”黄歇缓缓摇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她,她不会在秦王稷和公子芾、公子悝中做选择,她要的是全部留下。大秦的国土,她更是不容分割。”义渠王听到黄歇的话音中竟似有无限悲凉,他欲说什么,最终还是顿了顿足,叫道:“那我就让你看看,谁说了算。”说完,他转身骑上马,朝着咸阳方向绝尘而去。黄歇看着义渠王的身影没入夕阳之中,只觉得这半天晚霞,已经变成血红之色。义渠王闯入章台宫的时候,天色已晚,芈月正倚在榻上休息。义渠王用力抓住她的胳膊问道:“我问你,我、芾和悝加起来,和你那个秦王儿子,你选择谁?”芈月骤然惊醒,努力平息怦怦乱跳的心以及被吵醒后自然升腾的怒火,令吓得跪地的宫女们退下后,才甩脱义渠王的手问他:“你怎么会忽然问这种话?”义渠王却执着地问她:“我只问你,你选择谁?”芈月本能地想回避,然而看到义渠王此时的眼神,她知道已经不能回避,直视着他,一字字道:“我谁都不选择。三个孩子都是我的孩子,我不可能放弃任何一个人。”义渠王坐在那儿,整个人忽然沉静下来,那种毛躁的气质顿时从他的身上消失了。他一动不动地坐了良久,抬起头,深沉地看着芈月:“你是我的妻子吗?”芈月道:“当然。”义渠王问:“那么,你愿意跟我走吗?”芈月道:“不。”义渠王站了起来,高大的身形此时看上去有些骇人,他忽然笑了:“其实,你一直在骗我,对吗?”芈月道:“我骗你什么?”义渠王道:“秦国从来就没有属于过我,对吗?”芈月看着义渠王越来越近的脸,直至距离不足一掌之时,终于说了一个字:“是。”义渠王纵声大笑:“果然,老巫说的是对的,你这个女人,根本不可信,你根本就是一直在利用我。”芈月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义渠王,脸上平静无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