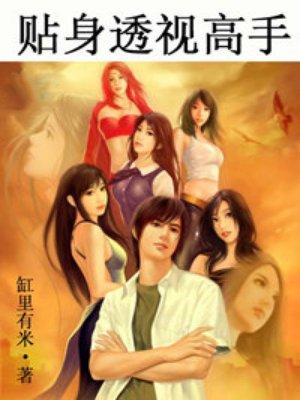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大宋不怂皇后被藩王和神犬赐精 > 一百四十三剑拔弩张(第1页)
一百四十三剑拔弩张(第1页)
却说赵鼎站在学舍的门口,候着那位一脸沧桑的黑面先生。
赵鼎一副恭敬的模样,反倒让那位先生拘谨起来。
赵鼎见状,心中大喜,直叹高手在民间。
“在下赵鼎,请教先生高姓大名?”赵鼎拱手问道。
黑先生刚说了自己叫“马五”,这赵鼎又来问名字,莫不是脑子有问题?
马五心中有些不悦,却也没表现出来,说道:“俺唤做马五,当不得先生唤‘先生’二字。”
再说话时,脸上已经没了笑容,一副冷峻的模样。
赵鼎见状,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他方才还以为眼前的高人化名马五,不愿意与他透露真实姓名。
可是瞧这模样,那黑脸先生也不似作伪。
忽然,马五一声惊呼:“你莫非就是临安城来的赵鼎赵相公?”看那惊讶的模样,分明神经弧有些长的亚子。
这声惊呼引来了许多学子围观,都想看看朝廷里的相公长得什么模样。
据说赵鼎当年背流放的时候,身边跟着一个俊俏的小妾不离不弃,从临安一路跟到了琼州,学子们左右寻摸着,想看看那传说中的红颜知己跟没跟来。
赵鼎被人团团围成了一团,这才找到了一丝丝熟悉的感觉,颔首捻须道:“正是。”
黑面马五脸色一红,略显羞愧。方才刚拿了人家赵相公的名字砸卦开玩笑,转眼就遇到了真人。不过赵相公看上去还挺和蔼,应该不会跟他算账,的吧。
马五憨憨地一笑,说道:“莫叫相公笑话,俺马五就是个琉璃匠,原本在这应天府城里面开了个小作坊。兵荒马乱地没了营生,成了流民。承蒙申之小相公抬爱,不仅给了俺一口饭吃,还让俺人模狗样地穿起了褂子当先生,其实就是个粗鄙之人,真真是当不得这先生二字。”
一通谦逊的话,不仅没有表达出谦逊,反倒让赵鼎尴尬得够呛。
什么叫“人模狗样的先生”?你骂自己不要紧,把穿了褂子的赵鼎也给顺带上了。
赵鼎是看出来了,眼前之人是真的没什么文化,是他自己太喜欢加戏,把那马五的话前前后后想了那么多,误做什么高深精妙的理论。
虽然看破了对方的深浅,但赵鼎依然保持着谦逊的姿态,问道:“老夫听闻先生方才所讲的道理颇为深奥,不知是从何学来?”
一说到学问,马五的脸上露出了憨厚且自信的笑容,说道:“俺平日里干活的时候就喜欢瞎琢磨,发现了许多奇妙的景象,却不知其中道理。其实这道理大抵也是懂得一些的,可惜俺没啥文化,只会想不会说,那些话却是申之小相公教俺的。”
赵鼎点了点头,这般解释就符合他的认知了,说道:“如此说来,讲这么一堂课,倒也难为你了。”
一个没文化的人,能把一大通道理记在心里,然后再讲述出来,需要很强的记忆力。对于上了年纪的人尤其如此,不下一把苦功夫,必然记不住这许多的内容。
不料那马五却摇了摇头,说道:“一点也不难为。当初申之小相公将这些道理讲与俺的时候,俺就觉得这些话就像是俺自己肚子里的一样,从申之小相公口中说出来,只听了一遍便全都记住了。相公若是不信,俺现在再与你说一遍。”
赵鼎连忙制止,呵呵笑道:“不必了,不必了。先生讲了这一天的课也累了,快去歇息吧。”说着就要与那马五告别。
马五的表现引起了赵鼎对应天府书院的兴趣。一个琉璃匠人竟然能登堂入室地给学子讲课,其中道理更是鞭辟入里,引人深省。
那么这学府之中,定然还有更多有趣的物事,倒是可以多去旁听几堂课去。
而马五仿佛没有听出赵鼎话中的言外之意,依然候在赵鼎身旁,嬉笑道:“俺不累,这这么点劳累算得了甚?跟俺在琉璃作坊里对着炉火劳作比起来,讲课就舒服多了,活儿轻松挣得还多,让俺再讲几堂课都不觉得累。”
赵鼎也不知这马五是真的情商低,还是在装糊涂,却也不好明着将他赶走,只好缓缓地踱步,朝着别处走去。
马五见赵鼎转身,紧赶了两步跟上,说道:“若是相公不嫌弃,在下领着相公在这学府之中转一转?”
赵鼎心中想道:这黑小子,路走宽了。
侧身一拱手,说道:“有劳了。”
“相公这边请……”
“相公请看,这里是食堂,就餐的时候只需端上一个盘子,去相应的窗口索要对应的饭食,一顿饭能吃上许多花样,花费还很少,端地是妙极……”
“相公请看,这里是藏书阁,市面上有的书,这里基本上都有。学子们只需要验明了身份就可以进去读书。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个藏书阁晚上也不关门,通宵达旦地有人值守,任何时候都可以来看书。只可惜里面的藏书花样虽多,数量却少,只许看,不许外借。”
马五介绍的时候,满心惦记的是那一套《梦溪笔谈》,当真是怎么都看不够。只恨自己笔杆子功夫不行,有心想要抄下来,却总是半途而废,不是字写不对,就是图画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