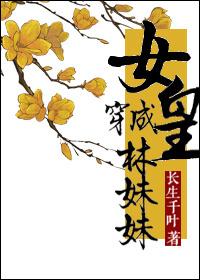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不争为争是什么意思 > 一百零八临别相聚(第1页)
一百零八临别相聚(第1页)
等了两日,学堂的人终于到齐了。丁园将里里外外二十几号人与邬忧引见了,邬忧亦自作了一番介绍,两边便算是相识了。因邬忧是初任,诸事毕竟不通,还是得先跟着丁园熟悉。尤其是学堂里各人的出身、秉性及天赋,都不是一两日就能摸准的。
既然邬忧有事可做了,戌甲自然不必再陪。还了丁园一顿茶后,便离开回山去了。之后的一段时日里,未见有什么要紧之事,倒也算安宁。这天,戌甲正在呆在产业里,忽然下面来报,说是外面有人指名来找。戌甲奇了怪,怎地会有人来这里找自己,还能指出名字?
随即到了产业门口,见到来人,果然是邬忧,方才笑道:“这会子你不是该在学堂看着么,怎么跑这儿来了?”
邬忧却上前一步,小声问道:“有说话的地方么?”
戌甲一皱眉,随即说了句跟我来。二人到了戌甲的住处,进到里屋后,戌甲问道:“到底什么事?”
邬忧反问道:“你接到调令没有?”
戌甲疑惑不解,问道:“什么调令?”
邬忧答道:“为灵封谷的差抽调人手的调令。”
戌甲来回走了几步,又问道:“莫非之前你我的推测应验了?”
邬忧掏出一页纸交给戌甲,并说道:“看看上面写的再说。”
戌甲接过来仔细看了一遍,交还给邬忧后,说道:“上面虽未明言,可意思很清楚了,就是为灵封谷而调的。既然你接到了调令,想来过些日子回山之后,造署那边也会发给我一张调令。”
戌甲抬手示意坐下谈,然后到屋外沏了两杯茶,端进屋子并放在案几上。想了一会儿,又问道:“你可打听到抽调去的人都在干些什么或是练些什么么?”
邬忧喝了口茶,说道:“我以前也问过被抽调去的师兄,依他话中之意,主要就是习练些基础的阵学。”
戌甲皱了皱眉,问道:“阵学?习练阵学做什么,莫不是进一趟灵封谷还要打起仙仗来不成么?”
邬忧吁了一口气,说道:“我哪里知道学阵学要做什么。相比于其他四学而言,山上于阵学尤其看得严实,即便是基础的阵学,也不会轻易教授。可眼下却一次抽调上去那么多人习练阵学,那只能说明这趟灵封谷的差有别于以往,必是相当之重要,且超出了你我这般人所知及所想的一切。”
戌甲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想了好一会儿,又说道:“按惯例来说,这等差都是派给道法修为在四层及以下的求仙人前去。虽然上下都不明言,可任谁都清楚,寻常出身的若是练不上第五层,以成就登仙人之姿的话,山上是不会在意其生死的。而这习练阵学又有可能是为打仙仗在做准备,看来被派上这趟差的人怕是真有性命之虞。”
邬忧也说道:“当初师兄与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只是没捅破那层纸而已。现在听你这么一说,便能肯定下来了。戌甲,若是过几日你也接到调令了,该怎么做?”
摇了摇头,戌甲说道:“真要被派了差,推是推不掉的,只能去了再说。况且到时候未就真会如你我刚才所想的那般,说不定是哪里来的情报消息不准,引得山上白白大动干戈一番。”
几日之后,戌甲回去山上造署,果然也接到了调令。从时限上来看,应是与邬忧同属一批的,都给了一月时间处理及交办事务,之后便要封闭修练,直至灵封谷开启。下山后,戌甲先回产业那里,找到管事的交办了相关事宜,并请吃了一顿酒。回山前,又特意去找左哲道个别。住处找不着,又去其常去的几处地方寻。最后,方才在一间单名井字的书屋外找到。
见到戌甲,左哲问道:“你怎地这会子有空来找我?”
戌甲示意去一边说话,二人找到一处僻静地方,戌甲才说道:“山上派了差,估计这几年都下不了山。我昨日才回来交办事务,今日特意来道个别。”
左哲摸了摸嘴,问道:“听你这口气,莫非是趟了不得的差么?”
戌甲摇了摇头,答道:“了得不了得,我也不清楚,只不过山上摆出的架势不小。”
沉默了片刻,左哲说道:“你急不急着回山?若是不急的话,我请你去家中吃顿饭,就当做为你饯行了。”
戌甲表示同意,二人便一同回了左哲的住处。左哲本是好吃之人,家中会常备些寻常的食材,自己也烧得一手菜。进后厨忙活了一阵,便端出了三碟一大碗来,外加一壶酱色的饮品。递过碗筷,又倒满了一杯,左哲一抬手,说道:“我煮的酸梅汤,尝尝。眼下已有些炎热,正好用来开胃。”
戌甲举杯尝了一口,皱着眉问道:“你这用什么梅子煮的,怎地这么酸?”
左哲灌下一大口,然后说道:“用的是自己腌制的山南大青梅,以小火熬煮三四个时辰,静置冷却之后,再装瓶放入冰水中待用。你也别嫌酸,我就是这手艺,不酸不正宗。”
吃了几筷子后,戌甲问道:“怎地不去三四点书屋,改去那井书屋寻书看了么?”
左哲叹了口气,边吃边答道:“没法子,近来三四点书屋的书已没法看了。满眼看去,柜面上摆放的净是些蠢得不能再蠢的书。只是,井书屋那里也好不到哪里去,净摆的是一笔名唤作未闻清写出的东西。”
吐出嘴里的骨头,用筷尖挑了挑牙缝,左哲接着说道:“那未闻清一眼就看得出来,肚子里没装多少棉绸,脑子里没藏几根针线,却偏要动手裁褂子。结果是一会儿袖子短了,一会儿领子没料子了。眼睛一红,荏地四处抓来都往上缝。长了再剪,宽了再裁。旁人要说不好看,反骂人没眼力,识不得这千色百料的绝妙配法。有一日真的穿了出去,内里膈应着不舒服,外面还被嘲作叫花子。”
戌甲笑了笑,说道:“从古到今,抄诗词的多了去了,又何必说得那么刻薄。”
左哲呸了一声,说道:“抄可以,不能乱抄。寻几句前人诗句,似是而非地拼在一起,前言不搭后语的,讲不出完整人话来。那未闻清要真有集唐的本事,你看我还会如此说么?牡丹亭我前后看了那么多遍,你几时见我骂过老汤抄诗了么?更不要说那未闻清光抄不够,还乱改一气。字词间的意思弄明白了么,就在哪儿改,简直就是糟践前人的心血。”
夹了一筷子入口,戌甲边嚼边说道:“这井书屋我闲时也去过,柜面上摆出来的多是些写酒豪剑仙的书,还曾翻过几本。经你这么一提醒,倒想起来那翻过的几本好像还真是署名未闻清。只是书里见不到几分仙气与豪气,倒是有扑面的俗气与小气。”
听戌甲这么一说,左哲哈哈大笑,说道:“知道未闻清为何总爱写些剑与酒么?因为漂亮好看。你看那虞姬,不就是细腰舞双剑,酒烫桃花面么,那多美啊!女子尚且如此,那男子就更别提有多美了,是吧?”
戌甲此时尚未回过味来,左哲又接着说道:“至于写什么无招胜有招的,那就更是瞎编了。凡招式者皆发于动之机,无招便是无机可发,机若不发,便动无可动,则以何取胜?写出此等蠢话之人,分明是脑中已然空空,却拉不下脸面,明言自己寸才已尽,反要硬拗。”
此刻,戌甲已然明白了过来,便笑着问道:“似未闻清这类笔法的书,在三四点书屋也不少,为何以前没见你骂过?”
左哲叹了口气,说道:“那是因为三四点书屋的蠢书实在太蠢,以至于掩护住了这类笔法的书。其实别管哪家书屋的书,但凡是未闻清这个路数的,都是那般鸟样。写书的稍能卖弄点文笔,连抄带编弄出些蠢故事。堆砌些华而不实的辞藻,拼凑些莫名其妙的词句,再借用些古色古香的名姓,好显出一个雅字。其实不管借的什么题材,用的什么笔法,但凡围着个一来编,那写出来的仍就不过是爽文罢了。任那些书被吹成第几名着的、作者被吹成什么大侠的,皆概莫能外。围着一来写,书中千人万物皆围着一转,实乃孩童视角,幼稚如此,便是比之长发女子亦远甚矣。还有什么把喝酒当潇洒,真是笑话!从来潇洒是指乘着酒兴干出漂亮事来,不干漂亮事那便是醉鬼,醉鬼潇洒?还有什么跟皇帝称兄道弟,岂不知皇帝乃贵胄之领袖,天下之表率,与皇帝称兄道弟便是脚踩贵胄而并肩俯视天下,且不说做到做不到,敢这么做的能活上几日?那些写书的蠢人到底知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再还有什么棋艺高超,动不动就让十二子的。怎么个让法,先挂四个无忧角,再点四个星位?师傅带徒弟下指导棋都没这么个下法。棋艺如火星,从来高手以命相拼而生,整日与些个臭棋篓子下,便如同顽石凿稀泥,哪儿能生出半点火星出来?凡此种种,举不胜数,偏生这些个蠢书本本皆被吹上了天,甚至要被排演成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