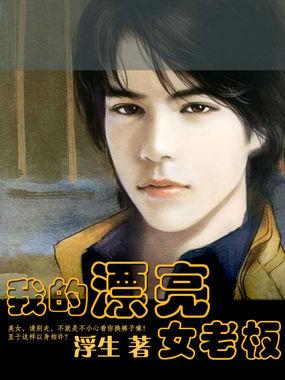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淑女诱夫作者东方玉如意 > 第27页(第1页)
第27页(第1页)
周朗用手肘支起头,好笑都瞧着她:“怎么,还想去看花灯呢?”“伤口都结痂了,应该也没事了吧。”“让我看看。”周朗说着就伸手去拉中衣的领口。静淑赶忙死死地抓紧了领口:“别……”自从换过一次药,发现伤口结痂之后,小娘子就不肯让他看了。周朗不敢用强,只能依着她,哄着她:“听话,让我看看恢复的怎么样。”“不要。”“那你说说为什么不让我看?”周朗不解。“因为……好丑。”小娘子自己都不敢看,那一道暗红色的血痂,像一条难看的大蜈蚣趴在肩膀上。周朗静默了一会儿,霍地起身穿衣,不再强求。静淑有点慌了,这些天他一直哄着她、宠着她,对她百依百顺,有时候自己都觉得好像不真实。现在他这副冷冰冰的样子像是回到了过去,让她心惊胆寒。“你……生气了?”她缩在被窝里,目光追随着他的身影。“在你眼里,我就是一个没心没肺,只贪图美色的男人么?”周朗系好腰带,飞快地梳好头发,就要出门。“我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夫君……夫……”眼睁睁地瞧着他大步出去,静淑心里凉飕飕的。小娘子落寞地眨巴眨巴大眼睛,无力地躺在床上,失神地望着他的枕头。不管这几日多温柔体贴,可他终究还是个有脾气的男人。正垂眸难过的时候,眼前光影一闪,身边柔软的棉被陷下去一块。“来,让我看看吧,我刚去烫了一下手。”他闪动着亮晶晶的双眸,搓着手去而复返。静淑一愣,不知该恼还是该笑,愣神的功夫周朗已经拉下棉被,长指灵巧的抻开带子,把右边的半幅衣襟展开。“啊……”突如其来的曝光让小娘子下意识地拉高被子捂住胸前欢快跃出来的白玉团。周朗只专注地盯着伤口,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查看了一遍:“伤口长得很好,血痂干爽,没有发炎化脓的地方。照这样看,月底应该就能自动脱落了。你可千万不要因为心急,自己用手抠,知道吗?”看他十分认真的样子,静淑觉得既可爱又好笑,微微点头:“知道了,我又不是小孩子。”小娘子乖巧听话,周朗越看越欢喜,俯身在她唇上亲了一口,起身时大掌有意无意地滑到了前胸捏了一把:“还藏?又不是没见过。”静淑小脸上腾地升起两片红云,拉起被子就要蒙住头,小声道:“你坏。”娇娇俏俏的大姑娘,跟鲜嫩的花瓣似的,让他怎能心如止水。大手按住被子,低头在她耳边道:“二月初天气暖和些了,就带你去给娘添坟,然后……给她生个孙子。到时候,你哪一处不是我的?”最后一句说的极为暧昧,话音未落,就含住小巧圆润的耳垂吮了一口。静淑小脸儿红透,眸光漾水,垂下长长的睫毛,不敢瞧他。羞羞怯怯的模样别提多诱人了,周朗身子蓦地就挺直了,抓了抓她的小手又放下,扔下一句:“我晚上回来。”就落荒而逃了。小娘子抿着小嘴儿合上眼又眯了一会儿,才缓缓起身。他要带她去上坟,证明是从心底接受她了,要让她去拜过世的婆母。正式成为周朗的妻子。暮色四合之时,周朗穿着青色官服回来。更衣之后,和她共进晚膳。自从换了厨娘之后,菜色焕然一新,荤素搭配,色香味俱全,府里的下人们再也没有敢慢待三爷和三夫人的。静淑受了伤,不必去上房请安了,小两口的日子安静温馨。吃罢了饭,周朗亲手帮静淑穿好狐皮披风,也把自己的貂裘大氅穿好,牵着她的左手出门。“真的可以去看吗?不会很挤吧?”静淑双眸亮晶晶的,既期待又紧张。“当然挤了,每年逛完花灯会回来,就被挤胖两圈。”周朗淡然说道。静淑停住脚步:“那怎么办?万一伤口被挤裂开呢。”周朗回头在她鼻尖上点了点:“放心吧,不是有你男人在么。”小娘子还是有点不放心,怯怯地跟着他往前走,却发现并不是去前院出府,而是去了后花园的方向。来到一座三层楼高的飞檐小楼旁,周朗定住脚步,静淑抬头去瞧,就见正门的牌匾上写着藏书阁三个大字。“我抱你上去,别怕。”周朗结实有力的手臂紧紧环在她纤腰上,暗自凝神提一口丹田气,足尖轻点地面,身子腾空而起,在瓦沿上若蜻蜓点水一般跳跃了两次,稳稳地落在阁楼房顶。“嗬……这,简直是飞上来的呀。”静淑惊奇地瞧着脚下。“看。”周朗扶着她坐在屋脊上,长臂一伸,指向不远处的一片灯海。“哇……好美呀!”静淑不得不慨叹,帝都果然名不虚传,元宵夜景如此恢弘大气,灿烂到耀眼炫目。“锦里开芳宴,兰红艳早年。缛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前辈的诗果然是真的,我在柳安州从未见过如此盛景。”周朗笑而不语,回身扯动早已备好的蝉翼丝,唤她回头瞧。静淑回眸,就见一盏鸳鸯戏水合欢灯从高高的树梢直直地飞了过来,即到眼前时,周朗大手一伸,稳稳地抓住花灯底座,托到她面前:“送给你的。”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让静淑回不过神来,捧着漂亮的鸳鸯灯,左看右看爱不释手,抿着小嘴儿偷笑。“元宵节不猜个灯谜怎么行?看这个,你这江南小才女能不能猜得出来?”周朗从雄鸳鸯的嘴里展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天鹅信使东飞去,口衔吉祥草归还,又见炊烟不见火,佳人如玺玉不换。静淑为了看清字迹,就把头倚在了他宽宽的肩上,周朗拢拢大氅,为她挡住寒风。“天鹅信使东飞去……哦,这个我知道了,鹅字里面的信使走了,上古传说中都说青鸟是信使,鸟没有了就是我字。诱夫第二十三计二月初,肩上的血痂果然掉落了,圆润的肩头上只是有一道浅浅的粉色痕迹,白璧微瑕,静淑瞧着微微皱起了柳叶眉。伤好了,她也没有出门,而是躲在房中做一套藕荷色的袄裙。若是让周朗瞧见,必定要被训斥。他不准她乱动,更别说做活儿了,其实伤早就好了呀。可是他太固执没办法,所以快到晚膳前他回家的时辰,静淑就会藏起来。今日终于把衣服做好了,也不用藏了,正在欣赏自己的作品时,他大步进门。“夫君,看我做的衣服好看么?”静淑像献宝一样拉住他袖子让他过来瞧。“你穿这颜色?有点老气吧。”周朗摇摇头,不太认同她的眼光,忽然反应过来:“这是什么时候做的?最近?不是说了让你好好休息,养身子的么。”静淑讪讪地收起衣服,乖乖服软:“身子已经好了,夫君不让做,我以后就不做了。”“完全好了?”周朗邪邪地一挑嘴角。“嗯,好了,怎么动都不疼。”静淑为了证明自己没说谎,特意动了动右臂给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