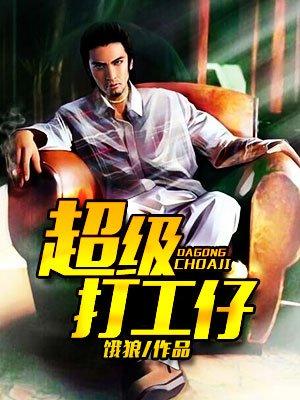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仇隙指的是 > 第61章(第1页)
第61章(第1页)
相比李雄,陈澈云就显得淡定得多,喝完莨菪酒的他浑身发热无力,软泥一样瘫倒在案上,脸颊绯红,他看起来像在很享受地笑,又似痛苦地浑身颤抖哽咽。
陈澈云从去年十二月就染了无欢毒瘾,李雄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以往他会识趣退出不听裕和王神志不清的呢喃细语,但是今天不行,百香楼是明面生意,无欢又是禁品,借着裕和王这棵大树遮阴才得以在各地暗中交易,所以不敢存太多货,现在进货渠道被自己人拦腰斩断,眼看百香楼就要变成无味楼,李雄都快急成热锅的蚂蚁了。
烛火被风吹动,亮如白日的天字号雅间忽明忽暗,谁也不知道这雅间的主顾一整天呆这里干什么,连李雄也不清楚。
李雄动了动嘴唇,还想再苦口婆心一次,却听案上的人魔怔地念着:“誓与汝南郡…共存…亡,誓与……汝南郡共存亡。”
陈澈云眼前的物件都是扭曲的,只有烛火还是那点烛火,粗糙的陶碗碰在一起,洒出酒花,明灭不定的烛火,墙上两个飘动的影子,永远清晰的脸,嵌入骨髓的誓言。
从香炉飘出的白烟包围着陈澈云,仿佛无数只来自阴间的手,拖着他坠入美梦。
李雄只好识趣退出。
过了一个时辰,一抱七弦琴的娼妓步步生莲开门走近陈澈云所在的雅间,习惯地捡起门口的金酒樽,一路避开被打翻在地的珍品荔枝和美酒,看见四脚朝墙的案几中间,蜷缩成一团已经熟睡的男子,男子的眉头紧紧皱成个结。
她不敢出声唤他,不踮着脚尖走路的杂音都有可能吵醒他,娼妓坐在男子身侧,把手里的七弦琴放在腿上,弹奏起来。
安定心神的琴音流转,陈澈云眉头逐渐舒展,女子却已经泪流满面。
一大清早,岑立堵着房门重复道:“你不准出去!”
岑立刚睡醒,衣裳还松松垮垮的露出半边肩膀,人模狗样的,挡住房间唯一的出口,王病起得比他早,早就收拾妥帖,哭笑不得道:“殿下别嫌弃我比较挑嘴,只是去买碗馄饨下肚而已。”顺道或绕路去看病。
昨天就见识了胡人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本领,每顿离不开酒肉,而王病只要一碗粥一个小菜就心满意足。昨天用晚膳时莫万空硬拉着所有人为太子殿下接风洗尘,王病为了不显特殊也去了,最后难逃一劫给灌了不少酒,有了廷尉牢狱两个月挨饿的前科,赶路过程又没有得到好的医治,腹痛得烙饼一样在榻上翻了一整夜,他不想醒来看到案上又摆着烈酒和肥肉,那样断肠之痛又要没完没了。
王病没能力跟岑立对着干,只好开玩笑道:“太子殿下,你要是不放心就叫个人跟着,我还指望你叫个会认路的带我走出祁府呢。”
岑立用力关了门。
啪!
“你要什么我叫他们买来就好了,郎中也给你请来,去里边躺好。”
“……”
寄人篱下少不得要受苦委屈,权力真是好武器,无形之中就把人收拾得服服帖帖,纵使王病一身都是银子也无处使。
莫万空已经准备好了早膳,亲自来请岑立用膳,岑立以昨夜睡不够要继续睡懒觉为由拒绝了,莫万空大清早碰一鼻子灰,用完早膳就不见了踪影。
跑腿的家仆端了两碗馄饨进来,岑立早就饿扁了,还等什么马上就开吃,王病细嚼慢咽吃了有一会,感觉腹部有热东西填着痛感也减轻了许多。
填饱肚子的二人在祁府回廊走着,王病的建议是找莫万空再商量商量画像的事,哪知二人去前堂扑了个空,莫万空已经早一步离开了。画像还满城飘动,岑立不能出府,二人就在祁府转悠。
“画像的事,我怀疑是林毅干的。”上次因为紧张没有好好欣赏祁府,四处闲逛着,王病再一次由衷感到祁府的奢华,规模之大细节之考究完全不亚于琅琊王氏的府邸。
岑立啐了一口:“真是阴魂不散!”
“这只是我的猜测。”在山阴的时候王病就觉得林毅对岑立不一般,又找不到合适的时机问问,而岑立压根没把林毅放在心上似的,离开山阴就对林毅追捕他的事一字不提。王病从来没觉得自己有过问岑立隐私的权力,这事看似就这么过了,没想到两个月后在汝南郡,画像的事竟然重复上演了!
两人不知不觉走到祁府后花园,几只鸟停在假山上啾啾叫个不停,王病走过依然昂着头叫,轮到岑立走过翅膀噗嗤一下剩几根鸟毛。
岑立:“……”
王病深思,并没有注意到这件小事,继续道:“林毅还不是元平候时,常年呆在汝南郡游山玩水,这是我在东观时候听到的,中书监常在我耳边唠叨……”王病突然一怔,想到去年洛阳城破,中书监拒绝崇延的招揽,上吊自尽了。
岑立偏过头看他,王病脸色像被人打了一拳似得难看,嘴唇不明显地颤了颤,开头语调就变了,岑立一眼就看出他在生硬地转移话题:“…元平候无官职,陛下对他一向很放任,他常年在外走动,会出现在汝南郡也不足为奇,所以画像一事,我想元平候的嫌疑是最大的。”
然而王病的只卡了一下,很快就又恢复以往说话的口气:“我想你可以告诉我你们在汝南郡最怕得罪的势力是什么,我不问世事一年多了,连现汝南郡太守桂冠在谁头上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