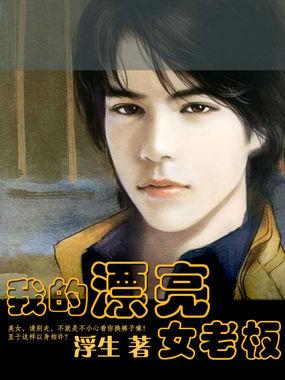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伯爵城堡干红葡萄酒价格 > 第85页(第1页)
第85页(第1页)
什么样的人,才能一直活得那样清醒?泽尼娅在那一瞬间,从洛伦·弗罗斯特身上,觉察到了某种永恒的力量,像凝固的时光,仿佛在轻蔑死亡。夜色降临,星辰浩瀚。两个年轻的姑娘躺在床上,却第一次没有进行惯常的夜谈。她们的心被不同的东西震颤着,并在这许久都未能褪去的波澜中沉入睡梦。温柔的夜降给生人迷离的梦,包容的夜赐给亡者欣悦的醒。洛伦·弗罗斯特夹着一支酒杯,瘦削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杯壁,厚重的云随之悄然散去,将被遮蔽的夜空重新显露。浩瀚星河横贯天际,半轮残月如淡白的骨片。城堡在夜幕中苏醒。从上锁的房间里、软木铺就的地窖里、丝缎装点的墓穴里,沉睡了一整个白日的亡者们醒来,走出黑暗的阴影。他们谦恭且小心地避开城堡的主人,不去打搅他静谧的独处,化作盘旋的蝠群,像陡然泼洒开的墨迹般飞向远处。洛伦·弗罗斯特饮了一口杯中殷红的酒液,色彩浅淡的唇在酒液沾染下显出惊人的危险艳色,半阖的眼睛既像厌倦又似期待。月与星的光照看着大地,从墓园流淌过的微风盘旋在他指尖。死亡的气息并不腐朽,可那冷寂与未知永远令生者恐惧。人们总是费心竭力地保存那具空荡荡的躯壳,仿佛这个注定腐朽的躯体能够重新延续生命。拥有越多的人越恐惧死亡,地位越高者越重视墓葬。他们把墓穴打造得坚实华美,用昂贵舒适的棺材盛装本该回归大地的垃圾,直到黑暗横空降临。生者们对活尸的恐惧轻而易举就压倒了一切,那些衣衫富丽的人费尽心思为自己打造死后的王国,却又被不留情面地从墓穴里拖出一一焚烧。沿袭了无数代的墓葬习俗就此被改变,每一具失去灵魂的躯壳都免不了在历经火焰后,化作一蓬干净的灰烬回归大地。这本没什么不好的,但似乎却将那些高位者对自己死后的幻想与抚慰狠狠地撕扯了下来。恐惧使人疯狂。洛伦·弗罗斯特饮尽酒液,在那殷红剔透的液体重新在杯中打着旋上升时,任由思绪下沉到七百年前。七百年前的佛里思特领在战争中生存。没有人认为佛里思特领能够仅凭自己抵御得了吸血鬼们,没有人不需要佛里思特领建立起新的边界线。罗伊斯公国的摧垮将危机感递到了每一个人的鼻子底下,早已习惯边境墙守卫的人们恐惧再一次面对战争,更恐惧新的边境再次倒下。于是,这就成了佛里思特领最大的筹码。然而如果没有恰当的引导,人们天性中的逃避与推诿会毁了它的。艾琳就是为此前往瓦尔顿领的,她足够聪明又有能力,更何况还有她的父亲瓦尔顿侯爵的帮助。一切原本都很顺利。教会是第一个伸出援手的,他们的援助至关重要,但洛伦·佛里思特不可能让教会像在插手罗伊斯公国那样与自己的领地紧密相连。他所拿出来的那些铁制符文与新的阵法是吸取了得自吸血鬼的知识而诞生的。教会的人无法从成品中看出黑暗的迹象,但与那位“研发出这些的天才牧师”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友好探讨就不一定了。早在得知教会来人之前,洛伦·佛里思特就为拉尼娅布置好了另一重明面的身份与死因。而他令拉尼娅放下手中研究的另一重原因,就在于此了。无论她此后再研究出什么,都不可能在教会的眼皮子底下正大光明的拿出来使用。洛伦·佛里思特接受了教会的援助,并与之维持在一个恰到好处的友好距离上。鉴于罗伊斯公国被攻破的真实原因背叛者显然与教会内部有关,否则他们也不至于如此费心遮掩。教会接受了洛伦·佛里思特维持距离的态度。教会是一方面,各个领主是另一方面,国王的那道册封旨意令许多原本与他接触的领主开始退缩。虽然他们并不知道洛伦·佛里思特到底怎么得罪了国王,但也完全能够从现在的情况看出僵持来。也许在他们看来洛伦·佛里思特是个以自己的领地与战争做要挟,来国王进行拉锯战的疯子。如果他失败了,被攻破的罗伊斯公国与其断绝的血脉就是他的下场,可国王不一样。但洛伦·佛里思特很清楚,那绝非是他得罪了国王而招致的。他的确救下了内勒·罗伊斯,但这件事未必就被国王知晓了。在边境被破的时候大开无忧之宴、接纳三个不战而逃的领主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洛伦·佛里思特更倾向于判断问题出在那位他从未见过的国王本身上,也许是一次与教会对抗的短视之举,又或者有别的什么原因。但洛伦·佛里思特没精力去再多去关注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