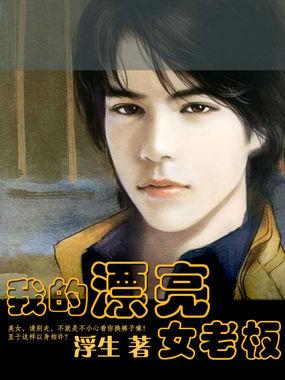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玻璃海棠图片大全大图 > 第12页(第1页)
第12页(第1页)
深色衣服的男人哂笑道:“绑架?我们就是把人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和快递差不多。”他说完又掏出打火机点了支烟。打火机在路灯闪过的时候发出一丝暗红色的金属光泽。这个打火机,她在家里见过。开了大约几分钟,车内始终无人说话,气氛处于紧绷焦灼甚至烦躁的状态,靠窗的那人手指不住敲打膝盖,目光移到了外面的公路上,深色衣服的男人抿着嘴,快速抽完了一根烟。面包车中间一排的座椅被拆除,乔勉曲着身体侧躺在当中,他低头看了眼。这个女人不吵也不闹,冷静得异乎寻常,而她的冷静在无形中将车内的氛围拉得更紧,好像他们才是趋于劣势的那一个。乔勉回忆刚才的场景,他们的车没有掉头也没有转弯,而是直接开往下一个路口。现在应该差不多九点四十五,两三公里后有条车流密集的十字路,但这个时间通常不会有交警。不知是不是车里昏暗无光的氛围过于压抑,司机打开了电台,也不管放什么,只想弄出点响来。她的头靠近车门位置,背对司机。面包车座椅下留有一点空档,她左脚的鞋跟可以碰到支撑的金属架,但险些发出声响,她稍微蹭了蹭,把鞋子脱了。男人抬头瞥了窗外两眼,她在快节奏的音乐里把腿往后抻了抻,座椅下狭小的空间挤压着她的小腿。车流声逐渐频繁,灯光愈发炫目,身边的车辆快速穿梭而过,发出空气撕裂般的声音。她的后跟沿着下方粗糙的地垫缓缓往前,电台里,音乐即将终了。突然,面包车左右急晃两下,司机骂了句脏话,车里的人顿时紧张起来,乔勉脚下狠狠一踢,司机原本踩着油门的脚再次受力,他猛一脚刹车,所有人都跟着往前冲了一下。与此同时,后方一辆轿车驶来发生了追尾碰撞,面包车又是一阵晃动。“操!”深色衣服的男人探身去稳司机的防向盘,后视镜中,碰到的另一车辆紧跟了上来,他抬头,前方正是红灯,车流众多根本无法硬闯。发生碰撞的那辆车停靠在旁,一名年轻女士走下车怒气冲冲地要敲车窗。乔勉用力把左脚从座椅底下抽出,她能明显感觉到一种撕裂的疼痛,她挣扎着从层层叠叠的胶带后发出喊叫,靠窗的男人把她死死压住按到角落里。红灯很快转绿,连窗都没有摇下,面包车飞速驶离。乔勉停止了挣扎,因为她可以确定,那个女人已经看到了车内的状况。录完口供,从警察局出来已临近半夜十二点,女警问要不要替她叫辆车,或者出车送她回去,乔勉摇了摇头。她走到门口,发现外面下起了小雨,她问有没有伞,警察马上从里面的架子上拿了一把递给她。从这里走到家大约十分钟路程,她感觉到了手t?机的震动,但是一直没有打开,无论是谁,她现在没有心思也没有力气解释。她拖着步子回到家,门口倚靠着一个人,手上拿着打火机正要点燃一支烟,打火机颜色暗红,泛出一圈很浅的光泽。直到她走近了,那人才反应过来:“吓我一跳,怎么声音都没。”他看向乔勉不由一愣,她光着脚,腿上有淤青,发尾沾着雨水并成几缕,神情疲惫至极,甚至用灰暗来形容也不为过。“乔勉,你……”“乔恒。”她面无表情地打断他,眼神定定看向门锁。“你怎么这么晚回来?我以为你在家,出什么事了?”“帮我开一下门……”她的声音有些嘶哑,带着点鼻音,她努力想对准钥匙孔,但整个人都在颤抖。乔恒拿过钥匙,发现她指尖异常冰冷。乔恒替她开了门,跟在后面急切地追问:“到底怎么了,你快说啊!”乔勉没有说话,就着楼道昏暗的缓缓侧目,眼底布着血丝,她一把夺过他手里的打火机,低吼道:“处理好你外面那些事,别引到我头上。”“什么意思?”乔恒不明所以。她把打火机笔直举到他面前,正中间三个字异常醒目——不夜城。乔恒脑子嗡地炸开:“是不是孟益那帮畜生?他们、他们有没有对你怎样?”她坐在沙发上,把头深深埋在掌心,还能闻到雨水潮湿、怪异的味道:“我累了。”乔恒蹲在沙发边,低声说:“乔勉,你告诉我,你……”“没有,出去。”“那你怎么这样了,你告诉我啊,要是他们对你下手我立马弄死他们!”“够了。”“乔勉……”“出去!”屋里瞬间安静了下来,他缓缓站起身,紧咬牙着关退到门外,他把烟头踩在地上,又用鞋底狠狠碾碎。对峙程何钧自打论坛交流结束之后就觉得自己没消停过,先是被校记者团的三个小孩子堵着采访了二十多分钟,后来不知是哪位老师提议,说明天周末,晚上正好开个庆功会。这次的论坛院里准备了很久,达到甚至超出了预期效果,院长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不知道,由着几个中青年老师去闹腾。吵吵嚷嚷吃完一顿饭后,徐老师说要回家盯着儿子做功课就急急忙忙走了,程何钧被众人拉去了市中心一家ktv。带头的是同事赵达,四十左右的年纪该会的都会,他自掏腰包叫了不少酒,起手先自己来了半杯,然后挨个打圈敬酒,知道的玩法也多,什么深水炸弹、三中全会一样不落。赵达有句常挂嘴边的话:面对学生,为人师表是职业操守,但是下了讲台,出了校园,教师本质上都逃不开是个“人”。眼下没有学生没有领导,他更加贯彻起自己的“人本主义”,赵达准备一口气过三巡的时候,手机忽然响了,他跑出去接了个电话,回来就拿起话筒冲屋里喊道:“马上有个人要来,大家都认识,玩好了说不定给我们买单!”随后目光一转,指着程何钧说,“小程,别睡,你可给我招呼好了啊。”程何钧从沙发上坐正了些一头雾水,赵达话刚说完,门口果真进来一个人,在喧闹的音乐声中嬉皮笑脸地大声说:“几位老师时髦啊,还知道来不夜城玩。”赵达冲上去和他狠狠握了一把手:“潘昊诚,潘老板!”潘昊诚连退了几步,表情夸张:“哎哟,不敢不敢,您是我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赵达扬手朝着他背上一拍:“客气什么,咱们现在是平等的,不乱辈分。小潘,说真的,下午论坛真应该把你叫去,优秀毕业生代表啊!”潘昊诚手往裤兜里一插,摆手道:“我就算了,我属于逃兵,一身铜臭味,怕污染了你们的学术气息。”“哪儿的话,搞学术也要钱,没钱搞个鬼呢。”潘昊诚和众人一通玩笑,左右逢源,依然是那副很健谈的模样。他与程何钧是研究生时的室友,但读到最后一年,不知受了什么刺激,毅然退学跑去青岛经商,但也的确发迹了。潘昊诚和几位老师闲聊了会儿,透过缝隙看到了后面的程何钧,两人相视一笑。他坐到沙发上,手肘碰了碰程何钧:“怎么着程老师,听说最近有情况啊。”程何钧喝了口水,疑惑道:“什么情况?”“装,继续装。”潘昊诚凑过来小声说,“我可都听说了,徐老师连人都见到了。”程何钧皱了皱眉:“她还和谁说了?”“没了,我现在是外人她才和我说的,你们院里根本没人知道。”程何钧点点头,有些心不在焉。潘昊诚思虑了一阵,看看他,又看看桌上的酒,沉声道:“别再弄得像叶子那会儿一样。”程何钧握着杯子的手紧了紧,没有说话。潘昊诚开了头就不再犹豫,取了个空杯满上,一饮而尽:“阿钧,有些事该藏着掖着就得藏着掖着,你老老实实和盘托出,让别人去想清楚考虑好,那谁替你考虑啊。况且……那事又不是你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