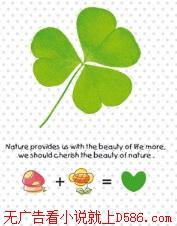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玉门往事番外 > 第18章(第1页)
第18章(第1页)
“挺热情的,”丁邱闻抱着书包,坐在了餐馆的凳子上,丁娇正在翻着菜单,丁邱闻说,“要是我真的回东北了,我觉得我会想徐嘉乐。”
“是吗?只会想他一个人?”
“妈,他很不一样。”
“嗯?”
“我已经很久没遇到关系这么好的朋友了。”
厨房里的油烟气味溢到了前厅,丁邱闻感觉鼻子里痒痒的,他已经到了应该叛逆的年纪,可是比起别的孩子,他是很能和丁娇和谐相处的,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他的身边只有母亲,母亲的身边只有他。除却母子的关系,丁邱闻更是姓邱的男人留给丁娇最贵重的礼物。
深夜,徐嘉乐坐在床边,看着熟睡中的丁邱闻。
这几天,徐嘉乐连忙碌的工作都顾不上忧心了,除了离婚之前一系列的麻烦事,他最关心的就是丁邱闻的工作和生活。丁邱闻早就睡着了,但是徐嘉乐睡不着,对他来说,熬夜是常态,而睡觉早就成了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客厅里的微弱灯光照进来,徐嘉乐刚好能看清楚丁邱闻的面容。
丁邱闻正在缓慢、无声呼吸,他睡得那样深沉,平躺在床上,盖着薄被子,他已经把加湿器关掉了,徐嘉乐再凑近一些,发现他的嘴角处有一点翘起来的角质,但唇部的其余皮肤舒展而光滑。
徐嘉乐靠着床头坐直了,把手掌放在了自己的膝盖上。
丁邱闻忽然睁开了眼睛,他吁出一口气,抬眼就看见坐在床边的徐嘉乐,丁邱闻问他:“嘉乐……你怎么还不睡?”
“你睡吧。”
“到底怎么了?”
“我睡不着,进来看看你。”徐嘉乐把放在膝盖上的手翻了过去,手心向上,他看着丁邱闻的脸,丁邱闻眨动着眼睛看他。
丁邱闻抬起右手,慢慢地,用手掌心贴住了徐嘉乐的手掌心,徐嘉乐一个激灵,然后,他的全身都僵住了,他没有一处关节敢动。
丁邱闻的五根手指紧紧扣在了徐嘉乐的手掌上,这时,徐嘉乐感受到对方不易察觉的抖动,丁邱闻居然……哭了。
徐嘉乐抬起头,看向床对面的墙壁,那墙上挂着小考拉的百日照。
徐嘉乐很用劲,他咬着牙关,尝试了好几次之后,才将手指从丁邱闻的手中抽了出来;他没有低头看向丁邱闻,但听得见他哭出了声,并且,声音很憋闷,他猜想,他应该是把脸埋进了枕头里。
“我去睡觉了,别哭了,快睡觉吧。”徐嘉乐说。
暗光之中,他看见了丁邱闻微微抖动的肩膀,他看见了他没有发丝遮掩的颈侧和耳朵,还看见了他被睡衣袖口遮盖住的手,以及,放在床头柜上的碎了屏的手机。
丁邱闻坐了起来,伸出手,一连抽了好几张纸巾拿在手里,他强词夺理,低声说:“我没哭。”
徐嘉乐的一只脚已经放在了卧室门外边,他说:“我去睡了,我要早起上班。”
丁邱闻没有说话。
“哥,等你上了班,很快就会好了,北京的工资还可以,攒点儿钱,要是你今后想回克拉玛依了,你就回去享受生活。”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还是要跟你说对不起,你来北京联系我了,我却没能帮得上什么忙,我爸妈前些年做生意赔了钱,现在过得也很一般,他们前些天还在说,要是当年没离开石油系统,现在说不定能过得更好一些。”
“嘉乐,”丁邱闻不哭了,他叫了一声徐嘉乐的名字,徐嘉乐只好后退一步,又转过身去,走到了他的旁边,丁邱闻穿着拖鞋坐在床沿上,说,“我没想到你还会叫我过来住,十多年没见了,你还是像以前那么好。”
徐嘉乐好似没有变化,他还是十几年前的徐嘉乐,他是个平庸的人,有些胆怯,有些保守,不够勇敢,但这不妨碍丁邱闻觉得他足以信任和依靠。令丁邱闻没想到的是,徐嘉乐在昏暗的光影下忽然靠近他,拥抱了他,他的耳朵正贴在靠近徐嘉乐心脏的地方,能听见他的中心器官泵送血液,发出有节奏和回响的声音。
丁邱闻没有说话也没有动,他一下接着一下,发着抖呼吸。
“哥,”徐嘉乐说着话,将他抱得更紧,“哥,我打算和她离婚了。”
丁邱闻闭上眼睛,长吁一口气,抬起胳膊环住了徐嘉乐的腰。
“她是性冷淡,她以为我也是。其实,两个人结婚都是为了佯装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可是后来我发现,我过不下去了,”徐嘉乐的一只手放在丁邱闻脑后,一只手紧紧搭在他肩膀上,缓慢地说,“真正的爱情都支撑不住沉重的婚姻,更不要说别的动机。”
丁邱闻把徐嘉乐的腰抱得更紧了,他的眼睛还是闭上的,几乎要再次睡着了,可他的脑子又很清醒,他问:“你们为什么会有孩子啊?”
“以为有了孩子就万事大吉,就人生圆满了,在别人眼里我们的确圆满了,可我自己很清楚,我的人生现在只剩下工作还是有一些意义的,孩子没有意义,婚姻更没有意义,什么都没意义。”
说到这儿,徐嘉乐的内心忽然一阵狂躁,他深深地吸气,丁邱闻苦笑,说:“你才是最应该去看心理科的那个。”
“我用不着看,我心里有数,要是我真的病了,那才好,可惜我没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