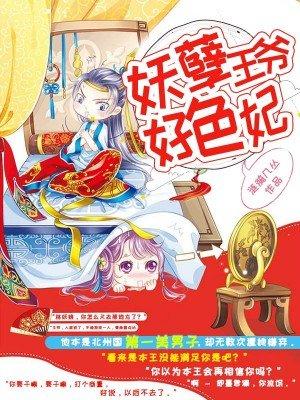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没有人像我一样全文免费阅读 > 第22页(第1页)
第22页(第1页)
那是当然。我说:&ldo;喂,喂喂,你应该告诉我你叫什么,从哪里来,我要送你回去。&rdo;她视我不存在,转身到冰箱里给自己取了杯冰水,咕嘟咕嘟喝下。&ldo;喝这么冷的水对伤口不好。&rdo;我忍不住提醒她。&ldo;你的烧也刚刚退,要注意。&rdo;她不为所动地看了我一眼,又倒了一杯。至此我可以确定她有自虐倾向,不过我也不是一盏好脾气的灯,一劈手就把她手里的杯子夺下,喝斥她:&ldo;女孩子要听话!&rdo;她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我不懂她在想什么,我只是直觉她有深不可测的心事,深得让人恐惧。恐惧归恐惧,我林南一到底不是吃素的。我打开冰箱门,把里面贮着的一大壶冰水拿到卫生间咕咚咕咚倒掉,走回来,拍拍手,得意地看着她。我的举动让她有点迷惑,微微地眯起眼睛看我。&ldo;你把水倒掉有什么用呢?&rdo;她终于又不紧不慢地开口,&ldo;你能二十四小时守住我吗?你不在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喝冰水,想喝多少喝多少。&rdo;她原来是可以一口气说长句子的。我放心了,对着她甜蜜地笑:&ldo;至少今晚你没得喝。至于明天,哼哼,你在不在这里,还很难说。&rdo;&ldo;那么我会在哪里?&rdo;她故意装傻地问我。&ldo;派出所。&rdo;&ldo;你要送我去派出所吗?&rdo;她问。&ldo;嗯。&rdo;我简短地说。她不说话,眼睛一闪一闪,我知道她在想对策。任凭她想破脑袋也没用,我早就应该采取行动,甚至在她受伤的当晚就该这么做了。上帝保佑,第二天一早,阳光明媚。我从客厅的沙发上爬起来,推门进了卧室,给她拉开百叶窗。她一下就醒了,醒了就抱着被子迅速地靠c黄而坐,摆出一副戒备的姿态。我拉把椅子在她身边坐下,趁着阳光好,细细打量她。说良心话,她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姑娘,张沐尔对我的怀疑,也有他的道理。我抱着纯欣赏的态度看她,她终于不好意思,脖子一拧,牵动了伤口,疼得龇牙咧嘴。&ldo;为什么离家出走?&rdo;我问她。&ldo;没有家。&rdo;&ldo;不管怎么说,&rdo;我拖住她没受伤的胳膊把她拉下c黄,&ldo;你马上给我起来,刷个牙洗个脸我们就出门,早饭你可以在号子里解决,他们伙食应该不错。&rdo;&ldo;我不去。&rdo;她坚持。&ldo;由不得你。&rdo;&ldo;你别逼我。&rdo;&ldo;嘿‐‐&rdo;我诧异,&ldo;凭什么?&rdo;&ldo;凭这个!&rdo;她忽然猛地扑向我的c黄,从枕头底下摸到什么东西‐‐是那把水果刀,她用它来对准自己的手腕,&ldo;物归原主吗?不如同归于尽!&rdo;&ldo;我想你搞错了。&rdo;我冷冷地,&ldo;我和你非亲非故,你这套对我没用。如果你真的不怕疼,就割,我有把握在你死以前夺下刀子。&rdo;我看她怔住,干脆再趁热打铁加上一句,&ldo;至于在那之前你喜欢在自己身上割多少刀,悉听尊便。&rdo;我想我必须好好给她上一课,向来自杀戏只会吓到关心你的人,对于他人,只会是闹剧。我的话是太过冷酷,也可能是让她想起了什么,她脸色灰白,唇齿格格打颤。我还等什么,一个箭步上去就缴了她的械。她跌坐在地,眼泪又涌出来,神情充满绝望。她的哭和图图是完全不同的,图图是山洪爆发型,她是冷静吓人型。但不管什么型,女孩哭起来我就没辙,我把刀子扔到墙角,伸手拉她。她甩开我的手,把脸更深地埋在膝盖里,像是要把自己团起来。&ldo;你别哭!&rdo;我只会这么一句劝慰的话,我自己也知道不管用。&ldo;你不肯帮我。&rdo;她呜咽。我叹口气,在她身边坐下,尽量和气地问,&ldo;为什么不肯回家?&rdo;&ldo;我真的没有家。&rdo;她答。&ldo;如果你不老实,我为什么要帮你?&rdo;她终于抬起头,直视我眼睛,那一刻她神情诚恳,让人无法怀疑。我听着她一字一句:&ldo;如果,你活了十几年,除了伤害自己和别人,从没做过任何有益的事,如果,你的存在只是令其他人疲惫不堪,如果,你走了之后,你爱的人就可以活得轻松、自由、快乐,那你,如果是你,你还会不会留在那个让你伤痕累累的世界?&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