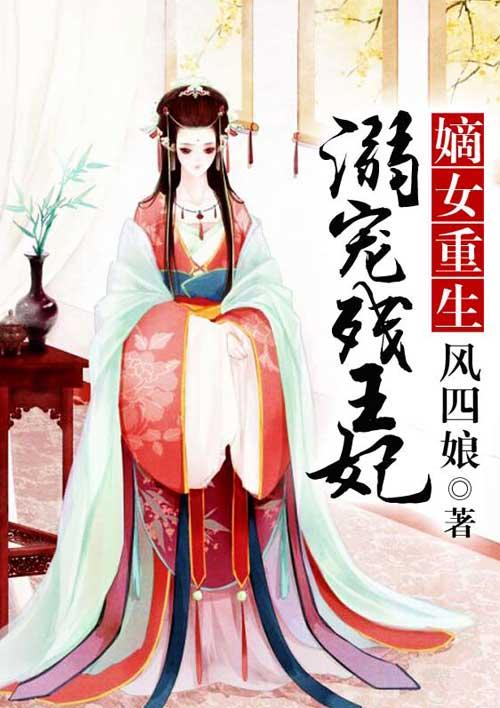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浮生若梦 byzbyz 含义 > 第2章 3(第1页)
第2章 3(第1页)
自从我搬进钱唐家,他头一次没回家。
钱唐以前就算再晚,喝得再酔,状态再差。第二天七点左右,他总是准时坐在厨房灌咖啡或喝清水。唯一没回家的可能,就只是出差去了。
今天正好是周末,我懒得回学校。漱完嘴里的余血就在他家打了会游戏。等中午大概十二点左右,听到门响了。我正在爆敌人的头,听到声音后特别想回头,但抽不出精力。
等我打完一局游戏想起这茬,客厅里也没发现钱唐的人影。跑上楼一看,他正脱上衣准备洗澡。看我门也没敲就走进来,钱唐不由皱了皱眉,但依旧像没事人似的问:“乳牙拔得怎么样?”
我冷笑两声,说:“牙疼了一晚上。”
钱唐听完后倒是走了过来,让我张嘴给他看看。我趁着钱唐手碰到我嘴的时候,吧唧把嘴合上。只可惜这家伙早有防备,完全没啃到他半根毫毛。
“刚拔了牙,你怎么还逮着什么吃什么?”钱唐弹了下我额头。
“也没什么逮着什么吃什么。我只是特别喜欢吃肥、肉、而、已。”
我尽量下沉语调,学着钱唐那种绕圈圈的讲话法,比如说我现在说我喜欢吃肥肉,而钱唐正好“食言而肥”,昨晚居然敢不回来见我。
不知道这人听没听懂,钱唐无声朝我笑了笑,先走进浴室洗澡。
我站在外面,巨想检查他所有衣服,但又有点拉不下脸,只得草草帮他挂起来时顺便看了眼。钱唐的所有衣服很干净,也没传说中女的头发和口红什么的。唉,就算真有,在我检查前,钱唐肯定也先拾掇干净了。
这是门里的水声已经停了,我赶紧再离他衣服远了点。盘腿坐在床上,从他各种笔记里拿了本假装看。
钱唐边擦头发边走出来,看了我眼:“看什么书?给我念念。”
我结结巴巴地念了几句《左传》,然后我憋不住了,说:“呃,钱唐……”
“嗯?有什么字不认识。”他走过来。
“你昨晚去哪儿了?”
钱唐若无其事地坐过来,先取我手里的书,顺手把手里的毛巾给我。我愣了下,才明白他的意思,慢吞吞地帮钱唐擦湿漉漉的头发。
他边翻书边随口问我:“大学第一周怎么样?”
“还成。”
我嫌弃湿毛巾粘手,跑下楼把自己的电吹风拿上来给。因为心里对他还有股怨气,手势就重了点,对准他眉毛鼻子吹热气。但钱唐好像一无知觉,他不吭声地任我摆弄。
等终于吹干头发,我倒是被弄得一股大汗。但依旧不忘问他:“哎,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
结果钱唐特别气人,他抬起眼皮淡淡反问:“特长生,我必须什么都要跟你解释?”
“我可是什么事都得跟你解释啊?!”
说老实话,我现在都没法形容钱唐是不是作风正派的人。因为他做事能轻而易举地绕开很多黑白观念,达成目的。我至今也不知道这是智慧,或是圆滑。但这样灰色地段的钱唐,却依旧有套很明确的原则。对我来说,就是你不能被钱唐的态度牵住鼻子走,你得跟他明说。对,什么都得明说。
比如现在钱唐听到我的回答,他沉默片刻。终于解释了几句:“我家老头来看我,昨晚被他捉住骂了一宿,所以没回家。”
我才不相信呢。
“你家老头男的女的啊?”
钱唐笑了,他往后倒在床上,玩味地说:“我父亲要是女的,我恐怕比你更担心。”
这也不是我第一次听到钱唐的父亲。
钱唐总是任人议论他自己的私生活,但与此相比,他对自家事通常一笔带过,防心挺重。但早在挺久前,我和钱唐的父亲有一面之缘(当时我俩都想买婴儿奶粉,真是天真无邪的时光)。除此之外,我还知道钱唐父亲是他们南方挺牛的法官之类,连我妈曾经都是钱唐父亲下属的下属下属之类。
我起了好奇心,不停对追问钱唐:“你爸来城里了?他住在外面?哎,你怎么不让你爸来你家住啊?他还喝奶粉吗?他最近有什么新吃的吗?”
钱唐闭着眼没搭理我。
我皱眉说:“你丫一定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钱唐终于睁开眼,他皱眉说:“你现在在我家住,我怎么让我父亲来?”
我愣住。内心隐隐有点火气升起。钱唐为什么不能让我见他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