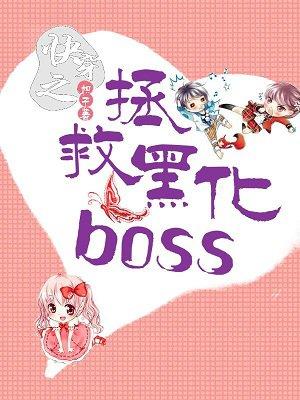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商户子走官途第100章 > 第39章 第 39 章(第2页)
第39章 第 39 章(第2页)
云崇青亲吻她的颊:“不困吗?”
“困,”温愈舒立马闭上眼睛,思虑着。
记恩下发的信条,通过自个岳父的关系,走驿站以极快的速度发往四方。孟籁镇上客满楼接了令,立时挂出概不赊账的木牌。
当天傍晚饭市时,两头发见白的老汉就跪到了客满楼门前:“大家都来评评理儿呀,客满楼的东家家财万贯,不养老母亲…五严镇云家,明知义子忤逆不孝,不加管束,还给他做靠山…没活路了…”
挨着士子山,孟籁镇上最不缺的就是文人士子。这方有冤,不一会,就聚集了不少身着襕衫的老中青。
“俺们也不求多,你指缝漏漏,能养活你娘就成了。怎么你就能这么狠心啊…是,你老娘贫苦,不及云家强势,可她…到底生了你啊…”两老汉老泪纵横,可怜极了。
有文士气愤:“百善孝为先,不侍父母者,无异牲畜乎。”
“鸦雀尚懂反哺,兄台将不孝子视为畜生,实乃辱没畜生。”
“客满楼有此东家,不来也罢。”
“哥哥呀…”一跛着腿的中年妇人拨开人群,扑在两老汉身,哭求道:“俺就这命了,你们别再…别再为难记恩了。他也是咻…是个苦命的娃,能有今天的日子…不容易啊。妹子求求你们了…别再来为难他了。俺不要他养…”
哭得是一把鼻涕一把泪,求得也是诚恳,就是咋愣赖在客满楼门口呢?
“听说这东家还是云崇青的义兄?”
“云崇青有此义兄,也是歹运。他一独子,就不怕哪天贼子逆反,叫他一无所有?”
“他可不怕,你们忘了人家可是沐宁侯府的小舅老爷。”
“哼…云记恩这般性情,与之一块长成的云崇青,德行怕也好不到哪去?”
周遭争议声愈大,三老货哭得愈伤悲。客满楼里有食客受不住,草草吃了点,结了账匆匆离开。站在柜台后的掌柜,神色平静,全不在意门外吵闹。东家已经给了指示,他照着来就成。
不过两刻,原座无虚席的客满楼里空荡荡。后厨没歇着,将食材都给煮了,装进食盒。十数伙计,拎着食盒,仰首挺胸地走出楼,面带笑容往城南、城北的破杂院去。
那里有不少小乞丐还饿着肚子,他们不会嫌客满楼脏。
次日客满楼,依旧准点开门。没有食客,就做菜送乞丐吃。事一传十十传百,就变成了客满楼东家狠绝,为让亲生的娘死心,不攀他,竟宁愿养乞丐,也不养亲娘。
仅七八日,整个山北省都知道了,许多文人笔诛墨伐,大有文昭十一年讨伐醉汉的那股汹涌。八家客满楼门可罗雀。还有人找上三里街,自称是石家屯人。云忠恒早吩咐过了,不许理。
九月二十,云崇青一行抵京时,山北又掀邪风。
“那个云记恩真是黑了心了,他也不想想他爷一个逃荒逃来的,能在石家屯安下家,靠的是啥?还不是石家屯那片人的好心。没他们帮扶,他爹想娶石家屯姑娘,做梦吧。”
“爹早死,他娘为了他都改嫁了。他倒好认了个富贵义父,连他爹的姓氏都舍了。”
“当初他不声不响走了,他娘眼都快哭瞎了,捶胸顿足恨自个没用,留不住儿子。如今那般富贵,就是给个千儿八百两银予他娘,又如何?客满楼,几十家几十家地开,他赚的盆满钵满,建金屋都不费劲。”
“要不是为了他师父传下的酿酒手艺,他以为云家会真拿他当个人看?”
这些,云崇青都不关心。在沐宁侯府安顿下来,即闭门读书。沐宁侯世子夫人听说记恩要在京开云客满楼,立时将东城武口街上的两间脂粉铺子清出来。
也是巧了,世子夫人那两间铺子恰在武口街和鹤立街交叉口上,门与鹤立街上的第一楼斜对着。记恩去看过,当时便拍了板,就这了。
“恩大舅,您可算是救了我娘了。”沐宁侯嫡长孙沐凛余,着一身灰色短打,一手揽着一只虎子,感激涕零:“我娘那两间脂粉铺子,已经亏了两年。虽然亏得不多,但可愁死她了。在此,我代我爹我小妹我外祖父母,谢谢您嘞。”
记恩都被他逗乐了:“这两年抽高不少。”世子家的小子,今年十三,瞧着都过他下巴了。
“那是,年初去了庆安,跟着我爹天天操练天天大肉,个子就窜猛了。”沐凛余低头看两堂弟:“你俩年初可是向我保证的,不会荒废练功,我在庆安就一直惦记着回来查检,哼哼…”
二叔家两个随二婶去了泊林看二叔,一时半会回不来。可惜了,不然一次就能撸四只虎。
“有祖父看着,我们做梦都别想颓。”大虎握拳,捶了捶大哥的腰板:“走吧,我们去练功房。”
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记恩笑问:“需要我去做个见证吗?”
大小虎不约而同坚决道:“不要。”挨打这种事,自己知道就行了。
“那恩大舅,我们先退了。”沐凛余拱手行礼。
“去吧。”记恩目送三人,直至走远才转身往東肃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