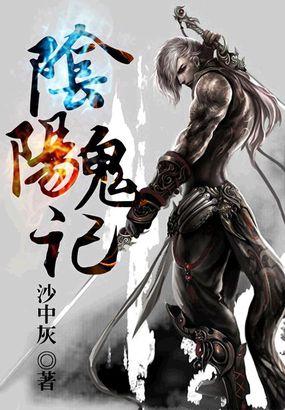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窒息gl 结局 > 第81页(第1页)
第81页(第1页)
她下巴渐渐靠在我的肩窝里,微微摇晃着。
“我当时快心疼死了,早知道就不该放她下车的那个傻孩子,都怪我当时太心软太宠她了。”
她念旧了一阵随即更加裹紧我道:“当初我跟你说的话我收回,你取代她吧,也只有你可以。”
“她……不是您的妻子吗?”
段亦然一下取下自己的戒指,开了窗用力扔了出去又很快关了窗,深深呼吸着。
“我有你就够了。”
空气短暂地沉默下来,就在我以为会这样风平浪静下去的时候,她突然一把推开我,冲击力令我猛地撞在窗户上滑坐了下去,看着她疯了一般地拧开门冲出去,不一会才在窗外看见她。只见她赤着脚焦躁地在窗下的绿化带里翻来翻去,没一会儿便跪在地上狼狈地开着手机上的电筒在那找戒指,外面天寒地冻的,连呼出的白气都清晰可见,她硬是在雪地里跪着找了半个多钟头才疲惫地捏着那枚戒指回来了。
一进门看也没看我,只淡淡道:“吃饭吧。”
两个人坐在饭桌上,我饿得连汤带水的一个劲往嘴里塞东西,段亦然则坐在旁边怀着恨意与愤怒似的不停地切割着盘子里的牛肉,连装饰用的西兰花也没放过,切的不如意又疲惫了,她突然将刀叉“啪”地摔在桌子上,又由于用力过猛而弹飞了出去。
我吓得僵在了原地,愣愣地看着她,看着她慢慢地捂住了自己的脸便一动不动了。
我咽了一口,等了好久,见她还是没有动静,便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拿叉子插中了一块肉,却听到很小的一声:“程尚恩。”
手一抖那块肉便掉了。
“程尚恩。”
“程尚恩。”
起初段亦然还是很正常的语气喊着,紧接着声音却越来越大,越到后面声音就越是癫狂,最后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咆哮。
她一边哭一边将手伸向裤子疯狂地喊着那个名字,我眼睁睁看着她满脸泪水地仰起头靠在倚靠上,露出的白净脖子上,布满了红晕和过于激动而鼓出来的青筋,双眼失神地望着吊灯,泪珠一颗一颗地顺着眼角滑落在锁骨上,一片水光。
突然她转过头望着我,可怜又无助地哑然一笑,道:“我想她了。”
我避开了她的目光,没说话。
“你是她吗?”
我拼命摇了摇头。
“啊……”她痛苦地呻吟了一声,随即胸腔震动起来,几近哽咽道,“为什么不是……你为什么不是……我要她……怎么办……谁来救救我……我快死了……”
说着她缺氧一样地一下掐住自己的脖子拼命呼吸着,脸瞬间胀得通红,舌头也作呕一般地往外翻,我吓得赶快站起来去掰她的手。
她却反手搂住我的腰,头一下枕进我的怀里揉蹭着“尚恩,尚恩”地喊我。
◇◇◇◇◇
过年期间段亦然接了一通电话,这通电话很奇怪,她只是拿着听筒安静地听了半个多钟头,期间一句话也没回复,末了才淡然一笑道:“表哥的手我道歉,好,那我就不回去了,您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说完礼貌地扣上话筒,抿着嘴唇也不说话,“登登登”的上楼又很快拿着一卷黄色的胶布,“嘶拉”一声拉得老长,不规整地就往玻璃上很难看地贴了一道,看见我在沙发上躺着看便道,“没事的话你去把碗洗了。”
我听后只能艰难地扶着沙发靠撑起自己,随便套了件散落在地上的衣服便拖拖踏踏地往厨房走去,没走几步一股热流便滑过大腿内侧“啪嗒啪嗒”地滴在地板上,我皱眉弯下了腰蹲着。
段亦然在背后不停地贴着玻璃,逐渐将这个房间的光亮一点一点的吞噬,厚重的窗帘一被拉上便彻底陷入了黑暗。
她回过身走到我身边道:“怎么了你?”
“那……里疼。”我抖着嘴唇道。
准确的说我全身上下已经没有一块干净的皮肤,连下巴上都是触目惊心的咬痕,我现在疼的已经在向施暴的人诉苦,以求来对方片刻的温柔,片刻就好。
“我帮你揉揉。”说着段亦然就势抱住我坐在地毯上,手伸进我单薄的衣服里绕着圈圈揉搓着,时不时又将手掌探近壁炉的火苗边取暖后复又在按上我的肚子,她靠在我耳朵边,呼出的气息温暖而又湿润,“还疼吗?”
我抖着牙关,“不疼。”
她亲了亲我的发顶,道:“不疼的话我们继续。”
我一下惊恐地回过身望着她,余光看到散落在沙发上的各色玩具后,眼眶便被一阵酸涩的液体狠狠挤压着,对方只是恶劣的一笑,食指刮了刮我的眼角。“好了好了,我骗你的,不要怕。”她眼睛紧紧盯着我这样说,中指却已经试探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