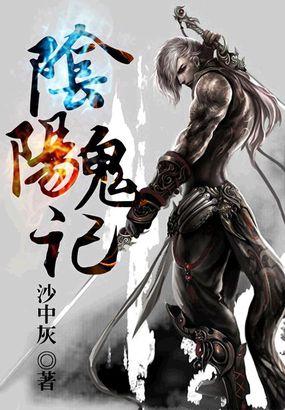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窒息gl 结局 > 第38页(第1页)
第38页(第1页)
可嘴里还是惯性地念念有词,“我错了,给点吃的……什么都行。”
这里连只老鼠都没有。
怪我,敲碎送来的餐盘割腕自杀却没力气下狠劲,现在半死不活地吊在这,忍受着饥饿的煎熬。
肚子又开始“咕咕”叫着,我捶了一下,也就这么一下,剧痛突然排山倒海般地袭来,我下意识按住胃弯下身的当口,一口浓黑粘稠的血就这么直接吐了一手,我像甩掉什么呕吐物一样甩了甩,扶着墙站起来蹒跚着走向洗手池,洗掉满手的黏腻,灌了几口凉水漱口。
无论我怎么若无其事,身体上的剧痛怎么可能控制得住,胃绞着痛不说竟开始直逼心脏。我一下滑跪下去,还死死地把住水龙头想要站起来,然而一切都是无用功。
蜷缩在潮湿冰凉的地面上,冷汗已经将唯一的衬衫从里到外地打湿,冷的开始一抽一抽地痉挛。
痛也只是一阵,多长我也能熬过去,只是心头的绝望又是多少人能体会的?
空间那么狭窄,不分昼夜的黑暗,除了排风扇再也听不到外界的一丁点儿声音,而我就这样抱着自己25岁的残缺身体,像抱着尸体一样僵硬……
◇◇◇◇◇
很久很久,我才能起来重新爬回墙边坐着,头枕着冰冷的墙面等待。
每次犯了错就会被丢在这呆上五天,不吃不喝,算了算,差不多了。
正这么想着,地下室顶头的门突然被人挪开,段亦然踩着楼梯下来,看到我怔了一下,却也没说什么,走过来蹲下身拿钥匙解我脚踝上的锁。
自上而下,这个人薄唇紧抿,睫毛微微颤动着,似乎还在生气。
我全身冻得冰凉,即使身上的束缚不在了也动都动不了,段亦然有经验地二话不说将我打横抱起。
一级一级台阶走上去,光亮逐渐刺眼起来,我伸出手想去抓住这些光亮,却发现想抬起的那只手早就不在了,而另一只的无名指上有我看了就想吐的东西。
放进滚烫的浴缸里,巨大的温差令我剧烈地挣扎了一下,却被不容分说地按了下去,段亦然解开我面目全非的衬衫随手丢进垃圾桶,挤了沐浴露在手心里将我全身上下都搓了一遍,到了关键的地方她恶意地塞进两根手指,我饿得没什么力气,低低喊了一声,将偏向一边的脸转向她,看着她面无表情地随意鼓捣我的身体,扣在浴缸边缘的手指痛得变了形。
腿在水里不断揪着蹬着,意乱情迷的脸不知不觉落入段亦然冰凉的掌心中,她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从痛苦到快感到高潮……
许久她低下头咬了下我微张的嘴角,伤口重新裂开,血腥味瞬间充斥敏感的鼻腔。
她一遍遍摸着我被打湿的头发,沉声道:“再对我说一遍你爱我,假的也好。”
我盯着她的眼睛,那里面倒映出的人似乎不是曾经那个站在天台上,悲伤地大喊“我爱你,段亦然!”的人了。
一切都变了。如果你知道的话,是否会后悔?
只要你有那么一点点的后悔就好,证明这四年你并非全然冷血地把我当一条专门发泄欲望连牲畜都不如的存在。
然而,当你把“爱”这个字当做情趣,在床上纠缠时逼着我一遍一遍说给你听时,我就知道你从未后悔过。
我拼尽力气,挤出我这辈子最后的笑容,对她说“我爱你”。
段亦然皱了皱眉,抽出了手指开始真正帮我洗澡。
其实我知道她的心情。
所有事情都如愿以偿的进行着,可效果却不像预期的那样令人身心愉悦,更没有振奋人心的成就感,她想要完全掌控,可人心怎么才能真正掌控?或者她曾经做到过,但摧毁不过一念之间。
她也知道我内心有多抗拒多疏远,然而行动上我又是顺从的服服帖帖,她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怎么都不是个滋味,所以只要我一旦表现出一丁点儿的心中所想,段亦然便会揪着那一点使劲地去挫败去打压,甚至不惜动用暴力去征服。
我懂她,可我偏偏不愿意称她的意。
我也是人,我也懂恨。
我跟她之间没有误会,我确实想跑,反正不是今天就是明天。
我就是不能让她得到我,就像我也从来没有得到过她一样。
段亦然把我从浴缸里捞出来,擦的干干净净后便拥着被子将我裹在怀里,一口一口地将薄粥喂给我,她不会帮我吹凉,只是舀起一勺就递到我嘴边,我自己吹吹在吞下去,再乖巧不过地靠在她身上。
喂完粥段亦然还是没松开我,反而拥得更紧些,我只是松松垮垮地歪着头看着窗外的雪景,鼻尖是她身上干净清爽的气息,有一丝丝的冰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