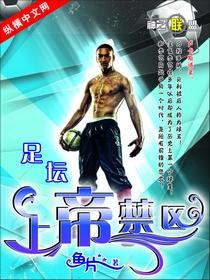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好看的灌篮同人文 > 第15页(第1页)
第15页(第1页)
两个人都不明白,但眼前这奇怪的情形却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纵是龙乘风身强体健,也觉不适,何况沈君玉本就文弱,操劳政务,已经烦扰不堪,又哪里经得起连日来的寝食难安?当沈君玉提出以后不在宫中过夜时,龙乘风立刻就答应下来。他冷淡地点了个头,却又在沈君玉走后,立刻召集一班侍卫,要他们专门护卫沈君玉的安全,一再叮嘱要注意她的饮食调养。随后,他又连连下谕到内务府,责令为沈君玉所建的府邸尽快完工,不能总让当朝尚书住在那种让庆国面子丢尽的破房子里。他把事情安排完了,忽然心中一片空茫茫,虽然拿着案上的奏折看了半日,却一个字也没瞧进去。他将折子愤愤地扔下,一个人跑到御花园打了一通拳,出了一身汗,但心头仍仿佛压着万斤大石般,沉得连呼吸都觉得很难。他想要找人诉说,却不知从何说起。烦闷之下,他喝令宫中侍卫陪他练武,可他才一抬腿、一扬拳,力道还没有发出去,侍卫已经滚出好几步,爬起来趴在地上磕头,口口声声:“皇上武功盖世,天下无敌!”龙乘风再也难抑心头愤怒,大喝一声,惊得整个御花园中宫女太监侍卫一齐跪在地上,口称万死。龙乘风纵有万千无名怒火,也难以对他们发泄出来。他一个人愤然走回勤政殿,斥退所有宫人后,用呼啸的铁拳,对着空荡荡得宫殿宣泄他心中那说不清道不明,不知因何而来,也不知要如何化解的郁闷。短短半炷香得时间,整个勤政殿被毁得一塌糊涂。宫人们不敢拦、不敢劝,只能隔得老远,听着皇帝声声负痛含恨的怒吼、呼啸不绝的拳风,只觉胆战心惊,彼此颤抖着相互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谁惹了皇上啊?”“不是刚打了胜战吗?”“好像也没听说有什么叫人头疼的大事啊。”“皇上拆了皇宫不要紧,要是擦破点儿皮,咱们拿脑袋也赔不起啊。”大家窃窃私语,分头找救星去了。有的太监飞一样向永乐宫那边报信;有的侍卫直接出宫,飞马奔向楚侯府;还有胆大心细的,想到皇帝的脾气是在沈君玉离宫后发作起来的,这解铃还需系铃人,就干脆直奔户部去了。永乐宫中正有贵客与太后闲话解闷,闻听此讯,一群诰命夫人、千金贵女一起站起身来,等着太后起驾。谁知太后只是闲闲地点点头,并没有动身的意思,她淡淡地说:“皇帝自小就是雷霆性子,说不定是哪个小太监惹他动了点儿微怒,这也没什么,不必如此大惊小怪的。”她的目光在众人之间转了一转,停留在一个清秀婉丽的少女身上:“哀家宫中有客,不便怠慢,雨柔你就代哀家去看看,皇帝是怎么回事吧。”萧雨柔微微一怔:“太后……”太后的笑容极为慈爱:“自然是你。皇帝常夸你温柔可爱,他就算被什么小人惹得动怒,有你劝慰,也会开怀,哀家放心。”萧雨柔垂头,施礼道:“领懿旨!”楚侯府中,楚逸得了讯息,亦不敢怠慢,忙骑快马往宫中去了。没有人比他更清楚龙乘风与沈君玉两人相知相敬之情。沈君玉一心为国,根本不肯考虑男女之私,更不肯为情爱折翼,自困于深宫,于是她干脆回避这些事,只视龙乘风为君王。龙乘风心地淳厚,但于情爱上,感觉却很迟钝,又不愿意勉强沈君玉,也决定只把沈君玉当臣子看待。两个人下的决心都很认真,也都很努力地想做到,只是许多事情,总不可能这般尽如人意。楚逸暗中早坏了隐忧,数日来,他见龙乘风郁闷非常,脸上再不见以往阳光般爽朗自信地笑容,而沈君玉一如既往,专心政事,但周身的冷意却越来越浓。楚逸看到了一切,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又能够为这两人做些什么。此刻,他虽飞速往皇宫赶去,但心中依然纷乱如麻,不知道如何应付狂乱的君主,也不知是否应该点醒仍在迷惑中的好友。户部算是现在京中最忙的衙门了,一来战后种种事宜处理起来十分琐碎;二来户部尚书沈君玉勤于政事从不懈怠,手下之人自然也就没半个敢偷懒了。只是近日来,户部的气氛一直有些怪异。大家依然忙忙碌碌,可是忙里偷闲,总会悄悄把视线投向他们年轻的尚书大人。尚书大人仍然勤于政务,尚书大人仍然不苟言笑,尚书大人仍然令人不敢亲近,却又不能不敬。只是,现在她常会拿着一份公文,看上半日也不翻动;只是,现在她眉宇间,总会有一种无法掩饰也无心掩饰的倦意,让人不由动容;只是,现在她常会在批示公文的时候突然就失了神,蘸满了墨的笔会悬在空中,忘了落下去,直到浓浓的墨汁污了公文,她才会猛然醒转,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每每令听到的人一阵心酸。户部上下人等,对沈君玉极为敬重,但又因敬生畏,即使非常为她担心,想要为她分忧,却一直没有人又胆子开口去问她忧从何来。这一日,宫中的侍卫忽然气喘吁吁地赶来,在沈君玉面前压低声音说了皇帝发怒之事。沈君玉只淡淡丢下一句:“皇上在宫中的喜怒不归我管。”然后她就继续去看手上的账目。两个侍卫听到沈君玉这句冷冰冰的话,不由变青了脸色,怔了半晌,待他们开口再求,沈君玉却忽然抬头,静静看了他们一眼。那样清澈而明净的眸子里,却有一种寂天寞地的冷、欺霜傲雪的寒。两个武艺高强的大内侍卫,被这双清冷的眼一看,竟是胆气全消,一起默然退走了。沈君玉平静地收回目光,再看向手中的账册。户部中人无不暗自佩服。这等色不动、气不变,却可屈壮士、服豪强的修养功夫、能臣气度,他们就是再学十年也学不到。只有沈君玉自己知道,她的一颗心已乱至何等境界。她眼睛望着账本上许许多多早已熟悉的数字,却根本不知道自己看的到底是些什么,每个字都已在眼中扭曲变形,化为龙乘风愤然的脸。那脾气大的吓人的皇帝,难不成真要把皇宫给拆了?他虽武功高强,但不知节制,胡乱发作,不知可会弄伤自己?伤了也罢了,反正他皮糙肉厚,自作自受,但如真把皇宫弄得塌掉半边,她岂非又要劳心劳力,筹钱维修?现在户部的事,已是一桩接一桩,叫人心力交瘁、应接不暇了,哪里还有余钱去给这荒唐皇帝修宫宇?她心中的念头纷纷乱乱,一时间竟不能抑制。她几次试图驱除杂念专心公事,但最终还是低叹一声,放下手中账册,闭上眼睛,心中升起了深深的无奈和疲倦。从来不曾感受过这样深的倦意,从来没有过这样无力的感觉,是因为多年的操劳至此终于负担不下去了,还是因为想到皇帝大婚的压力以致于承受不住了?皇帝是该立后了啊!可是……沈君玉静静睁开眼睛,眼中闪过一道清冷的眸光。她从来不曾惧怕躲避过什么,从来直言无惧、任事无悔,到如今,为什么迟迟不肯说明呢?既然是必须面对的,何惧坦然承认;既然是应该争取的,她又何必彷徨退缩迟疑呢?沈君玉忽然起立,语气平静道:“备轿,我要进宫!”楚逸一路进宫,通行无阻,来到勤政殿外,却被几个总管执事的太监拦住,太监们一个个挤眉弄眼,饱含深意地赔着笑,抢着同他说话。“楚大人,怎么连您也惊动了?其实没什么大事,平白让大人您跑了一趟。”“是啊,皇上这边已经消气了。”“对对,萧小姐一到,皇上立刻什么火气都没了。”“咱们原想进殿去收拾,可是皇上正和萧小姐说得高兴,咱们这些奴才,怎么敢败了主子的兴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