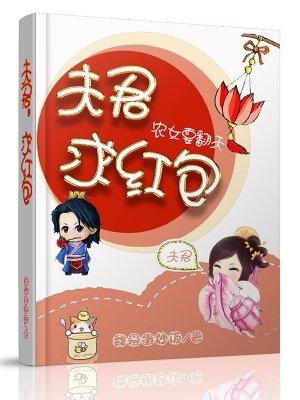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本侯有疾全文阅读 > 第71章(第1页)
第71章(第1页)
“不论世祖皇帝子孙,秦王子孙与蜀王子孙习武众多,上战场的不知凡几。蜀王子孙势大,蜀地兵马不可控,蜀国公之心难测,却也并非不可探得。赴鲜卑之行上上人选该是秦王子孙,而非蜀王子孙,因为秦王子孙多年不曾掌兵,偶掌一时,也不会夺了兵权去。定为蜀王子孙,或是因为蜀王子孙并不和睦,有机可乘,这机,便是蜀王第五子。
“以蜀王第五子、常乐王为前锋,封在北地,不着痕迹地收其兵马,不会引得蜀王诸子警觉,反而会让他们嫉妒不平,再封出去便容易多了,其所属兵马若是能收在手中自然是好的,受不得便安在北地,左右与匈奴战事频繁,你来我往,只需几年,这忠于蜀王子的兵马便能更换成忠于朝廷的兵马。
“这是阳谋,所有的算计都摆在了明面上,蜀国公却阻拦不得。蜀国公如果要反,他最多许出去郡王,裂土建国的亲王他是不肯的。左右都是郡王,为什么还要跟着蜀国公谋反?”
长公主点点头,没有说话,等她看完燕赵歌记录的东西,纸张拿在手里,冲着燕赵歌扬了扬,问道:“计谋乃是上上,当得侍中之位,既然看得明白,为何不记录上去?”
“此乃微臣愚见,不敢卖弄。”
“是吗?”长公主不置可否地低声问了一句,大约不是问燕赵歌的,也没等她回答,又走到废纸篓边上去了,看了看废纸篓里的纸团,又看着燕赵歌,问道:“这些是什么?”
燕赵歌心觉不好,硬着头皮道:“是,是微臣写坏了的……”
长公主定定地看着她,直看得燕赵歌心脏怦怦乱跳,才移开目光,蹲下身去,也没用内侍,自己伸手将纸团捡了出来。
“长公主……”
“侍中刚刚才说过,所言所想,皆可闻于我耳中,不曾有半分不便。所言所想可以,所写便不可以?”
燕赵歌只得将阻拦的话咽了回去。长公主啊长公主,你怎么不按常理出牌?
废纸团并不多,只有六个,长公主一一展开,三张是写错了字的,燕赵歌又重新抄写了一遍。一张是朝会前滴了墨渍的那篇《关雎》,另一张则是字迹工整没有墨渍的《关雎》,不知为何被搓揉了扔掉了。
最后一张,长公主虽有所准备,却还是看得一愣。
但曾相见便相知,
相见何如不见时。
安得与君相诀绝,
免教生死作相思。
长公主准备好的所有说辞都再说不出口。
殿内一时间寂静无声。
“侍中将这纸,送我可好?”她手捏着那张纸,极为用力,几乎要将攥在手中的部分揉碎在掌心。
燕赵歌吸了口气,道:“再好不过。”
“颠沛流离十载,家仇国恨,未有子嗣,侍中可曾后悔?”
“不曾后悔。”
“燕侍中言,所言所想,皆可闻于我耳中,不曾有半分不便,可有隐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