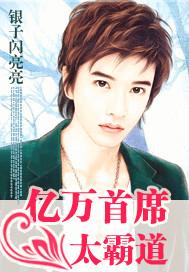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诡秘之主伦克r > 第15页(第1页)
第15页(第1页)
而今天的男主角,伦纳德·米切尔先生,二十年一遇地穿齐整套礼服还戴上了礼帽,经年凌乱的半长发也梳得服服帖帖——这令他的帅气值又上升了至少十个百分点,连克莱恩身为正牌恋人都忍不住脚步稍停想要再仔细看看。年轻又英俊的准新郎身着主体黑色的双排扣长礼服,袖口和衣角符合身份地点缀了一些殷红,同为黑色的修身长裤和皮鞋则衬得他身材高挑挺拔;礼服外套里面是洁白的衬衣和同色马甲,领口处按照鲁恩传统婚礼的习俗别着一朵鲜花:后者他选择了奶白色的玫瑰,和新娘手里的捧花保持一致。
……果然脸好穿什么都好看,连领口簪花这么骚气的穿法都能让他显得风流倜傥。
克莱恩在内心小小腹诽着。与此同时伦纳德终于结束了被训话抬头转向走道这边,目光落到了拖着长长裙摆缓步前进的身影上,一张俊脸仿佛瞬间被光点亮;明明还隔着老远,克莱恩却觉得自己读到了那双碧绿眼眸里跳跃的兴奋欣喜还有三分戏谑:
——赶紧过来呀给你靠近了看个够。
……自恋狂。克莱恩忍不住又编排了他一句,脸上却也不由自主被感染得露出笑容;少女伸手微微提起裙摆,加快了步伐,最后几乎是小跑着朝前而去——
——回到他曾经被迫离开、如今却将重逢的人群中去。
★☆★☆
“……这是有人在举行婚礼?”
班森·莫雷蒂一只脚跨进教堂的门口,停顿了一下,忍不住摸了摸鬓角所剩无几的头发,又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虽然说我们来得是晚了些,这会已经快中午了……”
……可什么人有资格在圣赛缪尔教堂举办婚礼啊?挽着哥哥胳膊的梅丽莎·莫雷蒂内心也转着同样的疑问。
“来都来了,我们过去看看吧?”班森转头询问妹妹的意见。
梅丽莎点了点头。
他们悄然加入了观礼的队伍。这时队尾也已零星多了几个穿着日常服饰的人,和前排清一色的漆黑礼服队伍风格迥异,约莫也是原本来教堂祈祷的一般民众。
梅丽莎踮脚去望布道台前的新人,一看之下却忍不住“咦”了一声。
“怎么了?”站在她后面的班森问。
“……不是……没什么,”梅丽莎顿了顿,还是忍不住问,“班森你……不记得了……?”
“不记得什么了?”班森露出丈二狒狒摸不着头发的迷惑神情。
……他大概是真的不记得了。梅丽莎无声地叹息。
她当然不会为此责怪她的哥哥:尽管那件事之后他们获得了足够一生衣食无忧的经济来源,但班森依然拼尽全力地学习、工作和照顾妹妹,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给这个家创造更好的条件。她知道,那是他冲淡悲伤的方式……身为一家之长,他不会也不可能停留在原地。
但她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正如同她永远不会丢弃夹在随身笔记本里的那三张再不会用上的戏票;而作为“那一天”的组成部分——她当然也不会忘记给他们带来噩耗的那个人。
——那个黑发绿眼、脸色惨白的年轻人,如今正站在布道台前,牵着即将成为他新娘的女孩的手,接受主教和在场宾客们的祝福;他英俊的脸上容光焕发,笑容纯粹没有一丝阴霾,和梅丽莎记忆里几乎判若两人。
他们离得远,听不太清台前的人们在说些什么。宣读誓词的环节似乎刚刚结束,前排的观众发出善意的起哄声,新郎转过身揭起新娘的面纱,捧起对方的脸,亲吻她——
一阵冰冷缓慢地流过梅丽莎的脊背。
在飘扬的白色半透明的面纱下,她看见了半张似曾相识的脸。
在理智来得及将所有信息排好顺序之前,巨大的、无可抵御的悲伤就重重撞在了梅丽莎心上。
一瞬间她甚至以为自己会脚一软坐倒在地——可是没有。她只是下意识地咬住嘴唇,防止自己发出任何不该发出的声音,眼眶却渐渐红了。
……这可以解释一切。她回忆起那双绿色的眼睛,敲开她的家门时,冰冷而沉寂得像一潭死去的湖泊;他下葬的那天……抬棺的青年失魂落魄地站在墓穴前的身影,一动也不动的身影,仿佛他的一部分也已随着逝者一同消亡。
可是为什么呢?她朝记忆中的伦纳德·米切尔无声大喊,你为什么还能选择牵起其他人的手?如果你一直……思念着他,这样做又将这个可怜的女孩置于何地?而如果你真的……重新爱上了别的人,不再沉溺于失去他的痛苦,那当然也……也是你的自由……
……可他这么好,克莱恩他这么好……你又怎么舍得忘记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