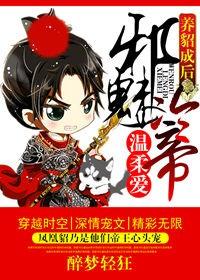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暴君(全三册) > 第35页(第1页)
第35页(第1页)
琴秀的两腮气鼓鼓,手心一翻,把多出来的头发藏进梳好的发髻里,然后去摸那柄发钗。狐媚子就是狐媚子!冉乔鸢无动于衷,随便琴秀给自己梳了什么头发,等身后没了动静,手一撑就要起来。但是被人压住了肩膀。“你要干什么?”琴秀这次用了十分的力气,眉头紧皱,压着人不让动,对着镜子里气愤不解的冉乔鸢很快开口。“少爷送了姑娘东西,姑娘也该回礼才是。就做件衣服吧,奴婢替姑娘去拿花样。”一本正经的模样。冉乔鸢懵里懵懂,脑子没转过来。——什么?这次回府,齐叶申明显感觉到观言的慌乱与紧张。“怎么了,是老爷叫我了?”他迈长了腿转进里屋,换了衣服才出来。美人身上总有淡淡的玫瑰香气,他沾了不少在衣服袖口还有领子。观言急的要死:“等着呢!小的说您被闻公子叫出去,老爷也不说话,意思一定要见着您。”齐叶申眉毛一挑:“看来最近情况真是不好。”居然有时间来关心他了。宋阶已经等了一阵子了,他坐在书房两旁的圈椅里,不在主位。和周长诵讲话的时候,他就是这么坐的,有点改不过来。周长诵去了西南,军队庞大,现在应该才出了京城不远。但他注定走的比那里更高更远。齐叶申进屋的时候,看见的就是父亲难得颓然的样子。宋阶很早就发觉了周长诵的转变,他不再胆小踌躇,眼睛里是天然的对权势的渴望。那些在废折上的批复显现出他生来帝王的气度谋略。他为此感到欣慰,但是又逐渐意识到危机。年少的帝王视他为敌人,蠢蠢欲动要从他的尸体上碾压过去,以此证明自己的地位不可怀疑。而缓慢腐朽的王朝制造出的官僚,则深深依赖于执行决断的内阁,对它唯命是从,认为它绝对不可动摇。周长诵是对的,他要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实力,收回本该属于他的东西。那就是战争。如果他还年轻,他还有筹码可以和帝王推扯,告诉他改变不是一朝一夕,血腥又残忍的方式后患无穷。但是他老了,而帝王没有耐心等滴水石穿,也听不进他的话。他期望一朝天翻地覆,用不可抵抗的力量把这个王朝中所有往下坠落的东西全都消除。“老爷。”宋阶抬起头,齐叶申是他唯一的儿子,他的母亲拼尽力气生下他,最后撒手人寰。宋阶于是让他随了母姓。小时候他就知道齐叶申天赋秉异,也一心想把他培养成才。但是后来他不得不放弃,比起什么步步高升,平平安安地活着才最重要。“最近还在念书么?”齐叶申低着头:“念了。”但是宋阶也没有问他念什么书,好像他只是突然想看看这个儿子。两个人都没有再说话,屋子里一直静悄悄。最后是宋阶喉咙有些痒,他不想在齐叶申面前咳出来,挥了挥手,意思让他下去。但是齐叶申这次没有听话。他站在屋子中间,脸侧过去看着坐在旁边微微弯下身子的宋阶。“父亲,我想带一个女人回来。”客人冉乔鸢觉得自己被耍了。夏日炎热,屋子里的窗户一直开着,外面一棵高高独立的树遮住了大半阳光,还算有点阴凉。但比起在周长诵身边的时候可差远了。这里没有冰,琴秀好像也没有想到要给她冰。冉乔鸢整个人燥热不安,完全没有心思去做什么衣裳。坐在边上的琴秀满心投入,好像没有看到对面的美人一直在不断调整姿势。她画完纸样子,又把料子照着上面剪下来,然后放到了冉乔鸢手上。“姑娘只要照着缝上去就好了。”手上被堆了一堆零散的布料,冉乔鸢整个身体都僵硬了。缝上去?但是琴秀没有等到她开口就出去了,留下一大堆各色的丝线,希望冉乔鸢顺便把绣纹也给缝了。手指捻着柔软的丝线搓了几下,冉乔鸢垮下肩膀,她真是不懂这个丫鬟的心。难道是那个男人很不喜欢别人送他衣服,所以琴秀故意让自己做,好让对方顺便不喜欢自己吗?怪人。衣服当然做不出来,但是琴秀很耐烦的样子,冉乔鸢说不会,她就一点一点细心指导,教她怎么对齐线脚,怎么收线才不会被看出来,包边又是怎么来的。冉乔鸢一头雾水,根本不懂她的心思,只能单纯认为对方是在打发时间。毕竟那个男人已经两个星期没有来了。缝衣服的速度很慢,冉乔鸢今天做半个袖子,明天做半个领子,但是陆陆续续总算有了一点雏形。她举着还差半截袖子的衣裳,居然莫名其妙生出一种自豪感。琴秀端来水让她梳洗,已经是晚上,冉乔鸢该睡觉了。因为齐叶申没有再来,也没有派人再来,根本像是忘记冉乔鸢的存在,所以琴秀心里开始认定,那天少爷叮嘱她好好照顾冉乔鸢,又给她买新衣,应该是最后的善意。她对冉乔鸢的态度也莫名起来,一边唾弃她的身份见不得光,觉得她拼命要少爷买下自己是不要脸,狐媚子,要勾引少爷。又觉得毕竟是容色姝丽的美人,以后可能就一辈子被关在别院里,再也出不去,渐渐对她同情起来。琴秀也是真的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女人,齐叶申不出现的日子,她居然有点喜欢起冉乔鸢,尤其是看到对方一脸懵懂,对一些事物完全不知不晓的状况,深深觉得自己就像在养育一个孩子。在别院无所事事,琴秀干脆教导冉乔鸢一些日常事物,拿来消磨时间。于是冉乔鸢被莫名其妙要求每日都描花样,剪花样,还要绣荷包,绣衣裳。她有点摸不着头脑,一开始还觉得新奇,琴秀又耐心,所以权当拓展技能,又出不去,除了在心里想一想到底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就剩下每天和琴秀对坐画花。她甚至还剪了一个姆明形状的布料出来,缝在一起变成一个小荷包。冉乔鸢这里兴致勃勃,因为暂时没有危险出现,过的还没有那么提心吊胆,另外一边,全军急速前行的兵马,已经快要抵达西南。周长诵坐在马上,看着探路的军士回来,向他禀报前路情况。“沿途村子都已被废弃,屋子里东西却是没有多乱,应该是村民知道兵临城下,所以都避难去了。”马儿不安分地在原地踱了几步,周长诵牵紧缰绳让它停下。避难。确实该避难。战乱无情,可是他却必须亲身经历,还要试图控制。下令行军至村落安整,周长诵坐在帐篷里,叫来了顾厉。原本他不打算带顾厉来的,毕竟京城里他只信顾厉和他的手下,宋阶虽然看上去已经完全不想再继续淌水,但是他湿过鞋子,周长诵想收回权力,首当其冲就是拿他杀鸡儆猴。但是顾厉坚持,他不能让周长诵身涉险境,哪怕对方有万分的把握。西南只是一个引子,周长诵必须让这个引子好好发挥它的作用。所以他不能败。西南比起京城更湿更热,身上盔甲沉重,又疾行数日,顾厉浑身散发着热气,掀开了帐篷的门帘。这里没有宫中那样讲究,周长诵身前的桌子上也只是放了一壶茶和几只杯子。照例是询问军中事务,回答完毕之后顾厉打算退下,但是周长诵叫住了他。“芙蓉鸟如何了?”周长诵难得问起,一路上对于亲征的渴望几乎霸占了他所有时间,一遍遍在纸上演算,行军的时候就在心里演算。站在下首的顾厉拱手行一个礼,是准备回答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