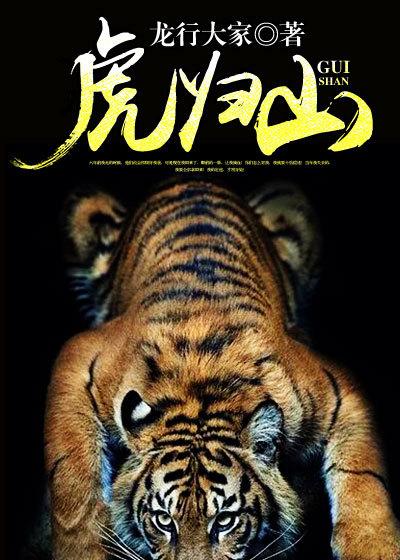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逢君穆陵路 > 第 60 章(第1页)
第 60 章(第1页)
指针滴滴答答指向亥时初刻,四下幽寂无声。裴沐珩手扶在小案,双目蓄着寒芒阴沉盯着她,周身罩着一种紧绷的威势。徐云栖本是为这事而来,因外祖父信笺一事被耽搁,自然也没打算瞒他,孩子的事还是开诚布公说明白的好。“外祖父之案兹体事大,万一有了孩子恐回头叫你我为难,同房后,我便施针流了出去今日你非要把脉,我实在不忍瞒你,故而决定据实已告。”这话一出,无异于五雷轰顶。裴沐珩只觉眼前闪过一阵黑线,仿佛有万千呱噪的乌鸦在脑门前盘旋,周身气血均往额尖窜。明明最聪明不过的人,对着这一行话怎么都体会不出意思来。她这是不想怀他的孩子?他难以想象他这边欢欢喜喜与她恩爱缠绵,她转背就能无情地把他们的孩子给‘流’掉。如果说方才章老爷子的事,他尚且能理解一二,避孕这桩已然是触及他的底线,他不能理解,更无法接受。那一贯沉稳的神情濒临碎裂。徐云栖说完这话,浓黑的鸦羽垂下,已不敢看他脸色。屋子里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对面那男人呼吸越来越沉,目光似刀子似的拼命往她面颊使,徐云栖有些顶不住了。果不其然,他宽袖骤然一拂,罗汉床的小案均被他一掀而落,他惯用的紫砂器具悉数碰撞在地,发出尖脆的碎声,紧接着那道颀长的身影罩过来,修长的手臂捏住她下颚迫着她看向他,“徐云栖,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裴沐珩双目猩红,面色阴沉得拧出水来,徐云栖望着这样的他,心底一片彷徨。决定动身来书房时,委实没料到裴沐珩反应这么大,在她看来,以裴沐珩之心性即便生气也能坐下来好好谈,直到方才他说出那番话,又气成那样,让她迷迷糊糊觉着,他对她对这份婚姻看得比她想象中要更重要。徐云栖心里有些乱糟糟的。恐他被气狠了,只得轻声解释,“二爷,你怨我,我无话可说,可我这么做也是有缘故的,我们可以选择要或者不要一个孩子,孩子却没有权利选择父母我们不能为一己之私,一时之快,枉顾孩子的安危。”“即便不能给她最好的前程,却至少要予她一个安稳的家,外祖父的事危险,二爷夺嫡何尝不是如履薄冰,我希望二爷能明白我这番心思”她不能让孩子重蹈她的覆辙。裴沐珩眼风锐利地劈过来,眼底霁月风光褪尽,唯剩排山倒海的暗芒,“如果我坚持同房,你待怎样?”徐云栖也知这会儿不宜与他硬碰硬,便轻声与他商议,“等尘埃落定后我们再好好养个孩子不好吗?”裴沐珩冷笑,“你就没想过多信任我一些,将自己彻彻底底交给我,你要信我能保护好你和孩子。”这话又将徐云栖本色给激出来,她视线静静与他交汇,舌尖在牙关抵了抵,语气恢复一如既往的平静,“我任何时候都不会把自己彻彻底底交给任何人。”外祖父自来便拿母亲章氏做例子,教导她始终保持一份独立和清醒,不要沦陷情爱。裴沐珩听了这话,猛地想起青山寺那晚,她对荀允和说,她这辈子不会因为任何人的缺席而虚度,那个时候心里半是钦佩欣赏半是酸胀难受,如今同样的话扔在他身上,只剩赤裸裸的刺痛。裴沐珩深深眯着眼牢牢注视着她,徐云栖已被他逼退在罗汉床的角落,纤细脆弱的胳膊瑟缩在一隅,黑白分明的杏眼水汪汪凝望他,白皙的面颊哭出一层霞晕,交织着泪痕,皓腕被他捏在掌心,柔韧的身姿如柳条般在他身下款款摆动试图挣脱却不得。他素来知晓她腰有多细,有多软,覆满水光的菱唇有多甜,体内炙热的血脉来回窜动甚至在叫嚣着渴望,他很清楚知道这会儿他想做什么。雨势隔绝了外头一切杂音,她被他禁锢在狭小的空间,暧昧一触即发,他们离得很近,鼻尖一动便可吸入彼此的气息,他甚至已嗅到了那股温软的体香,让人食髓知味。浓密的鸦羽轻轻颤动,那双熠熠如月的眼却始终清明且清醒,没有含羞带怯,也没有丝毫缱绻情态。裴沐珩眸光暗了又暗,唇角牵出一丝自嘲。强迫她?他裴沐珩,何至于此!眼底的怒火渐渐燃烧殆尽到最后只余一片灰烬,裴沐珩松开她,起身慢慢后退两步,转身扶着桌案,不再看她。徐云栖紧绷的脊梁蓦地松懈,轻轻吐了一口浊气,木木看了一会他修长的背影,她起身取下披风利落离开。深秋风寒,浓烈的雨汽从窗缝里挤进来,拍打在他面颊,裴沐珩不知不觉在桌案前立了半个时辰之久,脸上的青气已退,心底却空空落落好似荒原。当初熙王府的挑刺,满京城的嘲讽,她面不改色始终如一,那时他很庆幸自己娶了这么一位大方的妻子,如今真相血淋淋摆在面前。她只是不在乎而已。如果真是为了孩子安危推迟怀孕,他不是不能接受,可他深知不只如此,说到底她是怕孩子束缚了这段婚姻,绊住她的脚步。她为外祖父入京,为外祖父留在京城,那么寻到外祖父之后呢。裴沐珩不欲想,也不敢想。这一夜在罗汉床上浑浑噩噩睡过,次日凌晨天色还未亮,他照常醒来,意识有那么一刹那的混沌,他渐渐收整心绪扶案坐起。捏着眉心寻思许久,他扬声唤来王凡,这一开口方觉喉咙有些发哑。王凡很快进来了,裴沐珩脑海闪过昨夜的种种,怒火已消了大半,心口那股酸胀的情绪还不曾平复,气肯定是气着的,一时半会还没法好好与她说话,他淡声吩咐着,“去后院寻到夫人,让她将她外祖的画像画出来。”仅凭字迹无法断定(),有了画像与特征便可有的放矢。王凡很快退出书房?()『来[]看最新章节完整章节』(),循着朦胧的光色来到清晖园。立即让守门的婆子去请徐云栖。徐云栖昨夜至后半夜才睡着。该说的她都说了,能坦白的也坦白了,裴沐珩如若不能理解,她也无计可施。起先担忧外祖父辗转难眠,转念一想有了消息也是好事,后半夜总算睡踏实了,这会儿被将将起床的陈嬷嬷给摇醒,一听王凡过来,必有要事,二话不说翻身而起,匆匆穿戴唤来王凡,王凡将裴沐珩的意思转告,徐云栖当即便画了图,又嘱咐了许多细节。“这是我与外祖父的暗语,你只消发出暗语,他必有回应。”王凡拿着画像回到书房,裴沐珩看了一眼也没说什么,立即排兵布阵遣人分头去通州和营州寻人。出了这么大事,裴沐珩不可能坐得住,一早便去了朝堂,不得不说,范太医的谨慎是有道理的,便是裴沐珩明知牵涉宫廷,也不敢轻举妄动,他打算寻荀允和通气,商议稳妥再见机行事。偏生这个节骨眼,朝廷出了一档子事。历朝历代皇帝,为表彰自己功绩都有效仿始皇泰山封禅的夙念,当今圣上亦然,尤其他年迈体衰,恐时日无多,这个念头便更深切了,不过皇帝也很清楚,国库并不丰裕,封禅劳民伤财,不敢轻易为之,有人察觉皇帝心思,建议皇帝着人去泰山祭祀为帝王祈福,皇帝应允了。支持裴循一党的官员趁机纷纷上书,恳求皇帝立中宫嫡子为太子,准裴循前往泰山替他祭祀。裴沐珩看穿这是裴循的预谋,岂能让他得逞,他太了解帝王的猜忌之心,反其道而行之,暗中示意己派官员附和,就连燕平也上了一道折子拥立裴循,这下好了,众口铄金,裴循这位中宫嫡子已然是呼风唤雨,等裴循当上太子,朝臣眼里还有皇帝吗?裴循立在大殿正中露出冷笑。此举果然激起皇帝反感,恰在这时,秦王跳出来反对,“十二弟腿伤刚好不久,长途跋涉不利于恢复,不若还是儿臣代父皇出巡。”让秦王去是不可能的,皇帝神色懒懒顺驴下坡,“你说的不无道理,循儿还是在京养伤为要,这样吧”皇帝粗粝的手指在蟠龙宝座上敲了敲,目光最后落在荀允和身上,“荀卿乃百官之首,你替朕前往泰山,给朕,给天下子民,给大晋社稷祭祀祈福。”就这样,荀允和被派遣出京,裴沐珩不得机会与他细谈章老爷子的事,只得按下不表。
心里生着闷气,又怎么愿意回府。裴沐珩这一夜也歇在官署区。徐云栖不是没关注裴沐珩的动向,到了下衙的时辰便遣陈嬷嬷去前院问,大约薄暮冥冥时,陈嬷嬷灰头土脸回来了,眼神晦暗看着她,“爷今日不回来了。”徐云栖倒也没多想,毕竟裴沐珩时常不回府。到了第二日便是十月初十,王府有()规矩,逢十便在锦和堂用晚膳。这一日裴沐珩大多是不会落下的。徐云栖早早抵达锦和堂,时不时往门口张望两眼,平日裴沐珊在府上,家宴甚是热闹,如今她一走,显得冷清不少,裴沐兰性子内敛,李萱妍怀着孕怕勾出熙王妃伤心事也不敢吱声,谢氏向来稳重,徐云栖就更不用说了,一家人坐着便显得有些鸦雀无声了。碰巧管家这会儿进来禀道,说是裴沐珩有公务不能回府,熙王妃面上的兴致越发寡淡了。她百无聊赖搅动着筷子,时不时往徐云栖觑上两眼。忍了许久,宴后,熙王妃还是把徐云栖留下了。这应该是婆媳俩自成婚后第一次私下交谈。熙王妃面色还是和善的,“云栖呀,近来身子养得可好?那燕窝可日日吃了?”自上回被燕老夫人一激,熙王妃日日都给徐云栖送燕窝,徐云栖后来又给她施针两回,如今她这头风已许久不曾发作,她就当是给小儿媳妇的谢礼,其余媳妇也不敢说什么。徐云栖一眼看透熙王妃的心思,也不拐弯抹角,直言道,“母亲心里愁什么,儿媳心知肚明,儿媳便实话告诉您,我与二爷成婚虽有一年,实则半年后才圆房,这当中二爷又去过苗疆两月,实打实在府上的日子也不过四个多月,二爷公务繁忙,也不是每日都回府,今日您也瞧见了,所以您要盼孙子,怕暂时还没有。”徐云栖一席话让熙王妃心惊肉跳。裴沐珩竟然半年后才与徐云栖圆房。天哪。熙王妃摇摇欲坠,差点要坐不稳了,过去她生怕徐云栖不知轻重缠着儿子,哪知这丫头闷声不吭受了这么大委屈,熙王妃嘴张了半晌,心头一阵钝痛,“云栖此事你怎么从未说过?”熙王妃说出这句话时,心里有些戚戚然,当初她对徐云栖是什么态度,阖城知晓,如今又问这样的话,她自个儿面子其实很挂不住了。就在她以为徐云栖要嘲讽几句时,徐云栖还是那副云淡风轻的神色,“没必要说呀,这是夫妻之间的私事,我与二爷都需要时间适应彼此嘛。”熙王妃额尖一阵突突地跳,她不敢想象这事要被荀允和知晓会是什么后果,那位内阁首辅,可是在前段时日鞍前马后送女儿上衙,接女儿回府,这消息一旦传到他耳朵里,荀允和会立即把女儿接回去。熙王妃脑门一阵冷汗,不假思索将徐云栖的手握住,“云栖,此事是王府对不住你,珩儿那边我会去训他”徐云栖不着痕迹抽出手,笑眯眯截住她的话,“母亲,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让您去责备二爷,只是告诉您,您不必再催生,孩子的事我与二爷心中有数,您放心吧。”随后徐云栖便告辞了。熙王妃看着她背影,久久说不出话来。熙王从屏风后绕出来,也是满脸不可思议,不过以儿子的性格倒也不太意外。见妻子欲哭无泪,连忙安抚道,“好了好了,他们俩都是有主意的,你就把心揣肚子里吧。”熙王妃抹了抹泪,哽咽道,“我就是觉得对不住她当初我偏待她,她从不叫委屈,我身子不好,她也不计前嫌给我治病,她方才若是怼我两句我还好受些,偏生她没有”熙王哈哈大笑,“老二媳妇是个大度的性子,行医嘛,悬壶济世,见惯生死,这些事恐不在她眼里,你不去想,就什么事都没有。”熙王妃吸了吸鼻子,闷闷地看着熙王,问出她最担忧之处,“她心地宽大是好,可心里有咱们儿子么?”“这”熙王委实不好说。谁能料到当初无比嫌弃徐云栖出身的熙王妃,如今生怕徐云栖心里没她儿子,生怕她跑了。徐云栖回到清晖园后,银杏正从药房里迎了出来。“姑娘,奴婢将阿胶方子配好了,明日清晨便可下锅熬胶,每日吃上一片,整个冬日都暖暖和和的。”徐云栖揉了揉她脸蛋笑着道好。消食过后,主仆二人入屋洗漱,收拾停当一道往暖阁里窝着。更深露重,孤鸟扑棱着翅膀从琉璃窗外一划而过,银杏陪着徐云栖躺在被窝里,频频往窗外瞥,“姑娘,姑爷大约是被您气狠了,二日没回府呢。”徐云栖放空大脑,正昏昏入睡,“嗯”她迷迷糊糊应了一句。银杏回眸,往她怀里挤,“好姑娘,看在姑爷帮咱们寻老爷子的份上,要不要去哄哄他?”徐云栖听了这话,脑海有那么一瞬的空白。那晚她将一切前因后果剖析给他听,都已做好与他好聚好散的准备,那男人偏没有丝毫犹豫,就这么把整个事接管过去,徐云栖心里要说没有一点撼动那是假的。只是裴沐珩那频频叩击心灵的发问,令她很是不适。她从未好好审视过这场婚姻,随遇而安,走一步看一步,只要他答应她行医,给与她妻子的尊重与空间,她便觉得可以好好把日子过下去,而现在事情显然超乎她的预料。裴沐珩要的比她想象中要多。徐云栖茫然地想了一会儿,没理出一个头绪,揉了揉眉棱,翻身躺下。“哄男人这种事,还是算了吧。”她不会。亥时二刻,裴沐珩悄然回了王府。徐云栖习惯在这个时辰寝歇,裴沐珩也渐渐的把这个时辰点刻在了潜意识里。黄维恭恭敬敬迎着他往二房方向走,“二爷,今日要不要歇在后院?”夫妻俩吵架的事黄维心知肚明,这么一问显然是希望裴沐珩去跟徐云栖和好。裴沐珩止步在斜廊台阶处,抬眸看向夜空,细雨飘摇,无数雨丝在灯芒下扑腾乱舞,他俊脸隐在暗处叫人分辨不清,立了片刻,眼皮淡淡往清晖园方向掀了掀,折身回了书房。裴沐珩这两日心情甚是复杂。他这人从来都不好相与,但对着妻子却是和颜悦色的,他始终认为,真正有本事的男人绝不可能在妻子面前耀武扬威,是以他对徐云栖称得上温和体贴,尽可能给她撑腰,照顾到她的情绪,她要行医,他也说服自己去配合她。但徐云栖不肯怀孩子,委实踩在他容忍的底线。就这么僵持下去,有悖裴沐珩一贯的准则。若无其事继续去哄她惯她,咽不下这口气。他也不知是一种什么心理在作祟。他竟盼望着她主动示好,哪怕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