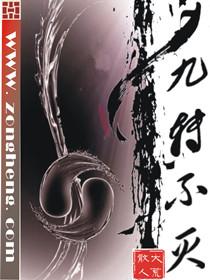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天下无双绝无二打一正确生肖 > 第1章 要饭预备起(第1页)
第1章 要饭预备起(第1页)
瑞荫城北街内围新开一家茶点铺子门店,名唤九团斋,老板小斯和迎客吆喝的小丫头们样貌都是顶顶俊秀,糕点也是新奇味美,男女老少慕名而来,才开张三月余,生意越发红火,隐隐有超越隔街李桃饼子铺争个“第一糕饼”的势头。
街头巷尾说九团斋老板白手起家年轻有为,样貌标志心地还善良温柔,可称人中龙凤。
任由枫蓬头垢面,一身破烂衣裳勉强多打了些结遮羞,腰上挂了个干瘪的破皮水袋,里面装的井水还剩两口,在九团斋门边檐下靠坐着。
外面下雨,人来客往,没人注意他。
这要是在亓京,像我这样潦草落魄浑身散发酸臭还来历不明的乞丐,到哪家酒馆不是要棍棒唾沫伺候再赶走的,是这的人都心善吗?到这儿以来,竟再没受什么欺辱了。
任由枫心里嘀咕,眼睛却注意着檐外雨势。
他打算等傍晚时候,雨再下大一点,客人不多的时候,向这听说心善的店家讨要一些卖剩下的食物果腹。
任由枫睁眼又闭眼,饥饿让他头脑发昏,手脚泛虚,可是腿上没结痂的刮伤粘黏着衣服,以及手臂隐隐的疼让他没法安稳睡过去。
他也不想睡过去,要是一睡睡到了天黑关门,今天就要不到食物了。初春的夜晚还是有些冷的,空着肚子会更难捱。
眼瞅着有一段没人来了,远处大钟响了两轮四下,已至日入,任由枫在心里做了几番预备——
待会起来,往店门口一站,再挺直腰板跪下,照着这边风俗的花拳手行礼,再以头抢地匍匐下去,说天佑老板安康生意兴荣,赏我口吃食吧。
然而他心里演示不知几番了,脑子却像是已经身体割裂开来了,下出再强硬的指示,手脚却只是意思意思般消极怠工地微挪了挪。
任由枫心中哀嚎,却只短促呼一口气。
任由枫还不熟练讨饭,甚至可以说从没讨过饭。
及冠之前他是彧国右相家的小公子,家族责任有上头两个哥哥给承担了,大哥是守关大将,二哥前年中了探花,封了个七品官,前途无量。自己只需中规中矩读读书不惹祸,家里嫡庶总共六个姐姐妹妹能把他惯到上天去。
他当纨绔子弟当得得心应手理所当然。
右相获罪斩首后,除了边关的大哥全家流放,他和二哥被人下毒,都没死,阿母却让他顺势假死出逃,之后全赖毛溜子领着养着。
毛溜子是乞丐,却算是个老江湖,拉扯着啥也不会的任由枫,一路避着官兵,跋山涉水向西北十几年前独立出去的墉城国去。
毛溜子知道哪里有破庙破屋,任由枫有地方睡,毛溜子懂些医,任由枫磨破皮的脚没疼多少天就治好了,毛溜子很会讨饭,还会算命杂技,不常能赚钱,但每每任由枫感觉自己饿到快死了,毛溜子找来了吃食,又活过来了。
毛溜子是受任母任姐之托拿钱办事,任由枫却仰仗他,叫他“毛先生”。毛溜子不应,说送你到墉城国咱就该别过了。
任由枫在逃亡的路上潦草及冠,除了头发终于得空梳理一下,身上已无多少体面。
城中富商贵妇的老嬷嬷和拿着棍棒的小斯们为了显得威风,很乐意在给主人的轿子开路的时候打打路边碍事的乞丐顺带吐干净喉里的唾沫。
任由枫每新到一座城,每又被欺负一次,就忍不住再委屈一番——卖货的店家怕影响生意赶咱没啥问题,我俩确实丑黑还脏臭……可走大街上碍着谁了嘛?走就是了嘛,咱不是在走了嘛…呜呜。一把鼻涕一把泪,袖子一擦,涂黑的脏脸再花一番。
不过即使如此,他还是更喜欢在路过城里待几天的时候。城里人多,吃的也多。
山林野地和无人烟的荒原中走的时候,风吹日晒雨淋的,双脚走到麻木了前路却像没有尽头一样,常常精疲力尽的时候却要加速,因为天黑之前得找过夜的地方。
险路可擅长削人意志,把人变孤魂野鬼的样子。
偶然迎面遇到一群土匪,瞧见俩人零零碎碎的破烂样,都不稀得劫他们,反倒是任由枫忽然晕倒碰瓷成功,蹭得土匪一次热水澡和一顿热饭。
想想那土匪大哥看着他毫无仪态狼吞虎咽时嫌弃的眼神任由枫就脸热,好丢人。
城里虽然容易被飞来一脚踹到胳膊,但好歹富贵聚集的地儿,贵人们盛肉的碟子蹭下的油星子都比郊外农户猎户半月的存粮顶饱。在城里,讨饭还是卖艺都方便。
毛溜子开始也安排任由枫和他分头讨饭,结果发现他讨不着饭净讨打,还容易迷路,三番两次带一脸伤晕晕乎乎的等他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