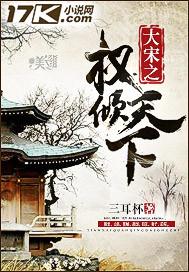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我只是为了小裙子! 作者他的耳坠免费阅读 > 第62(第1页)
第62(第1页)
但他确实一颗易碎的玻璃心,多少钱都买不来,所以急需自我疗愈。“我们去旅游好不好?”他对楚瀛说。“好,你想去哪里?”丁厌顿时满血复活,开电脑找景点做旅游攻略去了。这次旅行是为弥补夏天的遗憾,但丁厌并未选择热带岛屿或温暖如春的地区,而是拉着楚瀛直飞巴黎,下飞机换乘火车,去了诺曼底大区的北部,在海边遥望英吉利海峡和对岸的英国。这个季节来海边的人少,天空是雾蒙蒙的青灰,蓝色海面衔接着金黄沙滩,悬崖上生长着翠绿的冬青树。丁厌裹着围巾,在风里被吹红了脸,他得意地说:“这种人不多还风景好的地方,是你想来的吧?”楚瀛不给他留面子,道:“虽然很感谢你考虑我的感受,但这个地方我小时候每年夏天都来,没什么新鲜感。”丁厌用膝盖踹他,“你怎么给脸不要脸?”楚瀛:“我破罐破摔了,毕竟你经常说我不要脸。”丁厌不再接茬,他最近想通了,口角之争没意义,输了就输了吧!但输了总会想赢回来,没办法,他就是又菜又爱犯倔。到了温暖的酒店,他从行李箱拿出一套特殊的衣裳换上。那不能算衣服,因为一片布都没有,只是一些金属细链子合成的织物,串连的银珠披拂成帘,形似流苏,堪堪地遮挡住胸前。下腹是一条同材质的闪亮鱼尾,挂在腰上有些沉,“非人类感”十足。然而事实证明贴身穿戴的饰物还是选质地柔软的好,到了床上,那些链条在他全身硌出红印,难看到他想哭死,哀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过如此。楚瀛乐得欣赏他自我挣扎的凄楚模样,不过欣赏完了,仍然温柔地吻过那些交错纵横的淡红痕迹,手臂被碾出的褶纹微微凸起,皮肤带着略高于体温的热度。丁厌一鼓作气把自己扒光了,缩进被窝,还好是什么都不穿舒服呀,不然怎么对得起这么贵的床。楚瀛说小时候自己每年都来,并不是假话,第二天对方就带他去了一间位于乡间的小别墅,尖尖的屋顶、红色的墙,还有一座美丽的小花园。丁厌:“原来有钱真的能天涯海角、遍地为家……”“这是我母亲留下的遗产之一,我二哥不要,让给我了。”楚瀛道,“所以,你的确可以把这里当成家,想来就来。”房子请了当地人负责看管和打理,一通电话便召来了一对白发苍苍的白人老夫妻,给他们送来钥匙,和一篮子从自家农场采摘的新鲜果蔬。房子年代久远,灰尘重,还没有暖气,只能烧壁炉。丁厌在炉边铺了一张崭新的毯子,趴在抱枕上追剧。可是剧实在不好看,所以他抛弃了平板,调转方向,重新扔下抱枕,趴着看坐在沙发里看书的楚瀛。楚瀛热爱看书,那些书丁厌看不懂,所以他没想过与人分享阅读心得。趴累了,他仰躺着倒下去,三个抱枕叠出的高度,足够使他的头倒悬在枕边,在颠倒视野的内,继续注视着不远处的人。颠倒的世界很新奇,丁厌从中窥探出一丁点微末的异常——楚瀛并不是很专心,每阅读两分钟,就会朝窗户投去四分之三的视线。丁厌观察了片刻,问:“你在看什么?”“那扇窗前,以前有一张书桌。”楚瀛望着那里,“每天下午,我妈妈都会在那里工作,她不想我出去乱跑,所以会找一本书给我,让我坐在这儿看,等她工作结束了,就来和我讨论书里的故事。”丁厌的裤管宽松,小腿勾着前后晃荡,布料下滑露出一截小腿肚,“那张桌子现在搬去哪里了?”“忘记了。”楚瀛收回目光回到书上,翻过一页,“人的生活就是这样,你认为一成不变、索然无味,其实有些人和物,何时走出了你的生命,你不会知道。”丁厌低低笑着,“你这话说的,仿佛你活了好几十年了。可是你才不到30岁,与其缅怀往事,不如走入未来。”“未来?”楚瀛对这个字眼持无所谓的态度,问,“那你的未来里有什么?”“有我想要的一切!”丁厌的脑容量无法支撑他思考深奥的哲学命题,他提议,“我们来看电影吧?大西洋太美了!我想看关于大海的题材。”楚瀛应景地给他放了一部《碧海蓝天》。看到结尾,丁厌居然罕见地深受感动、湿了眼眶。然后一整晚都被淹没在影片带来的感受中。夜晚躺在咯吱作响的古董床上,他四肢紧紧缠绕着旁侧的人,他多希望自己能变成一床被褥或一捆绳子,把楚瀛严密地裹进身体里。“你贴得这么近,我没法睡觉。”“不行,我怕我睡醒了,你就变成海豚游走了。”“你多虑了,我和电影男主角不像,我没有穷尽毕生也要追逐的理想。”“孤独就是你的理想。”丁厌说完,诧异自己还能脱口而出这么文艺的句子,但不太应景,他感到无地自容,埋头在楚瀛颈肩乱蹭,“我不管啦,就这样……我就要这么睡……”但抱得那么紧,怎么可能睡得着,于是两人只能在床上滚来滚去,不知疲倦。过度放纵会使作息昼夜颠倒,尽管每天黎明才能在倦怠中睡去,丁厌却不想纠正或脱离这样醉生梦死的状态。那部电影唤醒了他内心的恐慌,他热爱现在的生活,傍晚起床站在阳台上俯瞰这座宁谧安静的小镇,他变得开始向往一成不变和乏味。好希望永远留在这里,生活静止在这一刻就好,什么都不要发生。可惜万事万物终归有尽头,十二月初,丁厌因姐姐打来的电话中断了无忧无虑的假期。丁茵餐厅的筹备进入收尾阶段,预计圣诞节开业,想请他回去帮帮忙。收拾行李的那天,丁厌找不到自己的耳机了,他在卧室里翻箱倒柜,找遍了每个角落,最终耳机没找到,倒是意外获得了一本纸页泛黄的日记。它落满了尘埃,被遗弃在柜子和地板间的缝隙里,他用沾了水的毛巾擦干净封皮,翻开的瞬间依然被扑面而来的粉尘霉灰呛得咳嗽。第一页是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的两个汉字,字迹一看就属于还在学写字的小孩,控制不了笔锋和力道,“楚瀛”两个字的偏旁部首严重分家,却又写得极其认真,一笔一画完整齐全。
我看一看,他会生气吗?丁厌转动脑筋,说不准自己偷看了会酿成何种后果。但以年份而论,恐怕连楚瀛自己都忘了还写过这么一本日记吧?他在还给楚瀛和先偷看一眼之间自我博弈,但没能抵抗住好奇心,翻开了首饰盒22餐厅开业在即,丁茵白天忙着招人培训,晚上还要留在后厨,和林睿讨论菜单和试吃新菜品。她着急让丁厌回来帮忙,是这些天每晚为了试菜而加餐,体重猛增了5斤,她可不能再这么吃下去了,只能求助于随吃不胖、还有丰富探店经验的弟弟。丁厌得了这份美差,天天有不重样的佳肴美酒换着品尝,快乐不必言说。但他也没闲着,度假时拍了很多视频,这些素材剪好了都是他的存货,每天都能发新作品。他消失了一月有余,再冒头,评论区的吃瓜路人和黑粉都已不见,只剩下铁杆粉丝们;纷纷赶来评论“失踪人口回归的第一件事就是撒狗粮[泣不成声]”“哥夫又带你去天堂浪漫了吗[看]”“我能不能变成你们的挂件跟着去”“下次带我吧”虽然热度降下来了,但丁厌其实更喜欢这种不温不火的氛围,愉快地保持每日8点准时更新。丁茵为新店开张正加班加点地给新员工做培训,丁厌一并留下参加,因为姐姐说可以给他发领班的薪水,有他这么个漂亮的人点菜上菜,是吸引顾客的活招牌。然而在指导餐饮服务这件事上,最专业的人是楚瀛,毕竟只有他是真的在餐厅里端过盘子。丁厌吃着切得薄薄的腌火腿肉,问:“你只是体验生活,为什么要干两年呢?”楚瀛把他们当作顾客,扮演服务生挨着给他们倒酒,说:“想试试看,靠打零工攒到钱能买得起什么。”“谢谢。”丁茵摆正酒杯,“那你最后买了什么?”楚瀛放下醒酒的玻璃器皿,回到座椅上,回答:“一只花瓶。”姐弟俩都笑了,一旁头戴厨师高帽、片着火腿的林睿点评道:“不失为一种行为艺术。”丁厌讲话不太分场合,他想着林睿是姐姐的旧相识,那也算自己人,说起私事并不避讳:“姐,你这几个月常回家吗?见过我爸妈没有?”“我边带孩子边工作,还要处理一大堆杂事,哪有时间回去?”丁茵瞧他的脸色,一猜即中道,“怎么?你们俩露馅儿了?”丁厌把八月初在家和他妈吵架的经过一说,担忧道:“我妈四个月没理我了,不会是不认我了吧。”“哪儿能啊,我爸不认我,你妈妈也不能不认你。”丁茵思索道,“我爸妈什么都没说,应该是还不知道,二婶并没有告诉他们。她这几个月可能过得比你还煎熬。”“煎熬什么?”“做心理斗争吧,唯一的儿子走上不归路,换做是我也会难以接受。”丁厌:“姐,你也这么封建吗?”“我只是打个比方,”丁茵说,“我不介意我的孩子和什么人结婚,但他们如果误入歧途、不思悔改,我会很痛苦。在你妈妈眼里,你和男人在一起,就是歧途。你可别盼着这种观念一朝一夕就能改变,只能靠时间去磨,日子久了,不接受也得接受。”她考量着,眼睛在他们俩身上打转,“你们是决定好要……?”“我们要结婚!”丁厌颇有信心道。“好吧,祝你们俩能成功。”丁茵举起杯子,敬这对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情侣。餐厅关门前,丁厌把林睿叫到旁边,给他看手机相册里的照片,问他见没见过这种食物。“哦,这是cepie吧,英国人过圣诞节时餐桌上常见的一种甜点。”林睿问,“你想吃这个?”丁厌压低声量道:“我不想吃,但我想做这个,你会做吗?能不能教我?”林睿:“这很简单,我回头把配方发给你,你家里有烤箱就能做。”“不不不,我不能在家里做,我不想被发现……”丁厌难为情道,“而且我特别笨,自己做不知道会失败多少次,我想你手把手地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