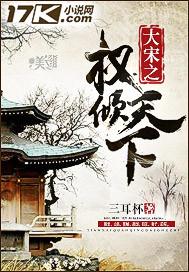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公主艳煞(重生)免费阅读 > 第89章(第1页)
第89章(第1页)
良久后,他小声又认真地说了一句:“十八不在,我一个人没有能力保护好你们两个,如果遇见危险,我怕我应付不来。”
“你倒是挺诚实的,”姬珧眨巴下眼睛,细细端详着他的脸,颇有些新奇,“所以你是在担心……我?”
说着又沉下脸:“还是担心你妹妹。”
宣蘅突然被提及,肩膀抖了一下,可还是没抬头。
宣承弈把视线移了回来,胸膛已经有些起伏不定,他莫名升起一股火气,这话问的,就好像她不相信他也会担心她一样。
可是喉咙中堵着的那句回答怎么也说不出来,她越是想听到什么,他越是不想轻易说出口。
姬珧看她把宣承弈逼得脸都快红透了,一声轻笑打断,她转过身向前走,状似无意地环顾四周,语气平平道:“那也要回去,我买的东西都落在说书先生那儿了,去拿回来。”
宣承弈低头一看自己的手,这才发现之前买的那些东西的确忘记拿了。虽然不知道骄奢淫逸的公主什么时候把身外之物看得这么重,但买那些东西的确花了不少银两,连金宁卫都觉得肉痛就可见一斑,他没办法,还是转身跟了上去。
好在回去的时候东西还在,说书摊子那已经没有人了,方才摩肩接踵围观的人都已经散去,酒楼里也空空荡荡的,只有地上的血迹印证此处才发生过一场闹剧。
也不知那二人最后怎么样了。
宣承弈把多于之前两倍的东西抱在怀里,头被挡在后面,声音却从那里传过来:“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姬珧有意无意地看了看四周:“我还没玩够呢。”
说完,她继续向前走,宣承弈的视线被遮挡住,只好侧过身子扭头看路,见到二人离他已有几步远,赶紧加快脚步行到姬珧身边,姬珧扬了扬唇,心情似乎颇为愉悦。
“本……我已经想不起来你刚到我身边时是什么样子了,但你现在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是武功水准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姬珧先是翻旧账,然后突然夸赞他,夸赞完又毫不客气地刺儿他,可谓一波三折,宣承弈的脸色变了又变。
但他没功夫跟姬珧置气,只是紧张兮兮地看着四周,恐怕会发生什么变故。其实他心中明了,他的确被她驯服得失去了许多棱角,开始变得不像原来的宣承弈。
而这种变化,不知是好还是坏,不知是不是出自他本心……
他忽然开口,平淡的语气听不出任何情绪:“金宁卫的武功都在我之上,你要是嫌我没用,现在就赶紧回去,别在外面当个活靶子了。”
他这么自然地坦诚自己的无能,姬珧还有些适应不了,她眨了下眼睛看着前头,莫名起了护短的心,尽管刚刚是她贬低了他。
“阿朝来公主府的时候见过你一面,他私下里跟我说,你筋骨不错,要是从现在开始勤学苦练……没准也能练成十八卫的水平。”
苦练多久她特意没说,贺朝的原话是:“此人根骨不差,如果把他放在暗厂十年,兴许能达到金宁卫的水平……大概吧。”
有多不确定?像贺朝那么惜字如金的人,“兴许”二字都没能表达完全,末尾还要加一句“大概吧”,由此可见一斑。
姬珧是为他找补,谁知宣承弈完全没有把这段话放在心上,他一听到从公主口中说出的“阿朝”二字,脑袋空空,然后便觉得后槽牙一紧,霎时露出不耐的神色,语气也没那么恭敬了。
“阿朝又是谁?”
他在“又”字上加了重音,鬼知道他咬牙切齿得又在较什么劲,姬珧以为他只是单纯的询问,接道:“是一个很靠得住的男人,比你强太多了。”
宣承弈停住脚步,斜眼看她,姬珧根本没注意他在发脾气,自顾自地往前走,走出好几步远都没回头。
宣承弈忽然觉得自己很没趣,连他自己都觉得酸,要是真问清楚了,公主大抵还是那句话,关你什么事。
她根本不懂他在气什么。
或许也不是不懂,就是在装傻,亦或者是压根不在乎。
他终是咬了咬牙跟上,心里自己给自己盘逻辑,是了,他没进公主府的时候外面就传言公主养了很多男宠,虽然他除了有数几个,别的一个没见着,可是他一次也没踏足过清林苑,说不定那里有很多日日夜夜等着侍奉公主的男人呢。
什么阿朝也是其中之一吧?
如果比他先,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宣承弈好像把自己说服了,他重新走回到姬珧身边,因为叠罗汉一般的礼盒高高垒起,根本看不清前路,所以只是凭借身边人的反应认路。
忽见姬珧睁大了眼睛看着前面,他不知发生了什么,心头一凛,紧接着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一声马儿的嘶鸣声——是马儿发狂和滚动的车轮轧着地面的声音。
周遭已经传来此起彼伏的惊叫,有人被马车冲撞开,发出惨叫声,突然发生的变故让人猝不及防,宣承弈能感觉到马车是冲他们而来的,情急之下,他顾不得怀里的东西,将东西一抛,拉着身边最近的两个人闪身躲到一旁。
马车疾驰而过,便是几个呼吸之间的事,有人骂骂咧咧地指责纵马之人,被冲撞开的路人都有些狼狈。宣承弈心有余悸,转头一看,脸色骤然一变,手中拉着的人哪里是公主?分明是战战兢兢的宣蘅,还有一个惊魂未定的陌生人,再去看对面,早已经空无一人。